2025年7月,译林出版社推出长篇系列散文《江南器物志》,图书面世当月,即入选“中国好书”月度推荐书目。这是一部以文字构建的“江南版《清明上河图》”,由著名作家、江南文化学者徐风创作,经《收获》杂志“江南器物”专栏连载,并入选2025年度江苏省重大题材文艺创作重点项目。出版后,作品接连入选《新京报》书评周刊主题书单、百道好书7月榜、《文学报》好书8月榜等多个图书榜单。
在研究、书写中国紫砂多年后,徐风将目光拓展至更广阔的江南器物谱系,以“器隐镇”为文学道场,从科举、稼穑、节庆、风俗、嫁娶、餐饮、庭院、家具、服饰、舟车、礼品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书写南方温润又激烈的山水间那些人与物,器与神。此外,徐风先生的另一著作《布衣壶宗——顾景舟传》(全新增订版,曾获2015年度中国好书),也将于今年10月顾景舟诞辰110周年之际,由译林出版社全新推出。
8月16日,《江南器物志》的新书分享会在上海书展举行。本书作者徐风,携手《收获》原主编、浙江工商大学教授程永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一起,探寻江南百物与万千世相,以及器物背后生生不息的中国精神与生活美学。活动由东方卫视新闻主播秦忆主持。译林出版社社长葛庆文、总编辑张遇出席分享会,葛庆文代表出版方致辞。

与器物有缘——陶瓷店的小小守夜人
器物连接着民生——从童年时与外公同在陶瓷店守夜开始,徐风就对此有了模糊的印象。徐风的外公是一个陶器店的老职工,陶瓷店就是一个器皿世界,冬夜漫长,年幼的徐风常随外公在店中守夜。在诸多器物的环绕中,在来往的各色人群中,徐风学会了和外公一样用一把茶壶喝茶,懂得了很多器物方面的知识,也看到了器物背后的民生百态——正品的陶器比较贵,1毛钱一只碗,次品只要6分钱,对彼时务农的普通人来说,省下来的4分钱可以打小半斤的酱油。
器物与人之间悠长细密的故事,由此静静蛰伏在作家心中。在参透了紫砂精神之后,徐风愈加感受到其他器物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紫砂还不能代表江南文化的全部,其他的器物,特别是老百姓一直在使用的老器物,逐渐进入他的写作视野。书写一百多年来江南古镇上老百姓的“器物生活”,丈量器物脚下的土壤,以及器物背后的世道人心,是《江南器物志》的创作初衷。正如程永新教授在“江南器物”专栏开栏时所说,“器物是冰冷的,人心是滚烫的。”“百姓日用为道”,器物只有包裹在世俗的烟火中,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才有光彩,才有精气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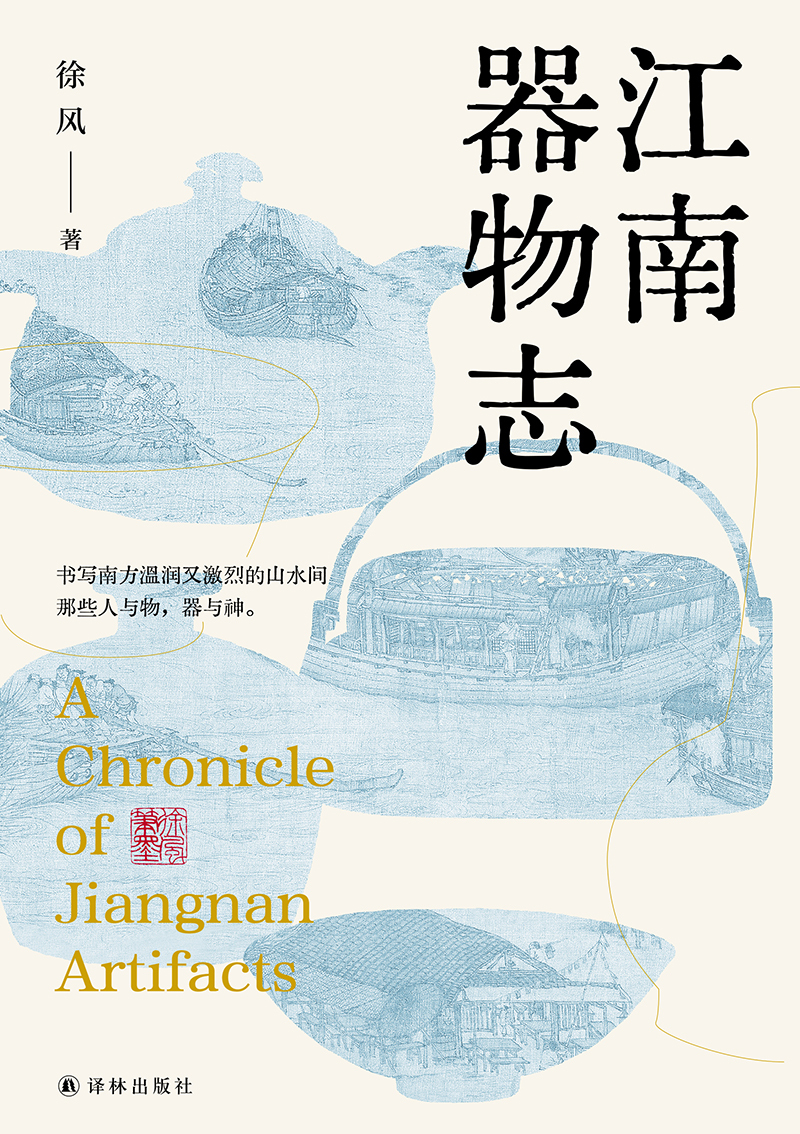
《江南器物志》
民间的江南而非文人的江南——从普通人的视角重塑江南器物史观
徐风的器物观其实是一种由器物折射的历史观。研究沈从文先生多年的张新颖教授,在这两位作家身上看到了相似的历史观——关心像你和我这样的凡夫俗子的生活历史。
张新颖说,有读者反馈,读完徐风先生的作品会联想到沈从文写文物,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阅读现象。就像徐风讲他小时候的故事,提到陶瓷的好坏、穷人和富人,这样的故事就类似于沈从文的故事。沈从文幼时看到小银匠打银器时一边打一边流泪,对此充满疑惑。在生活这条长河中,沈从文渐渐知道,任何一件器物,如杯子、碗、碟子,制作人的喜怒哀乐会不知不觉地融到器物身上,也正因为对人的爱,沈从文很喜欢器物。正如徐风所说,器物与人的悲欢喜乐连在一起。
比起个体的历史,普通读者往往对帝王将相的历史更感兴趣。张新颖指出,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说,“二十四史”里面没有普通人日常生活历史。那么,什么是普通人日常生活历史?我们怎么样来写普通人日常生活历史?在张新颖眼中,日常器物就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徐风的写作聚焦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器物,选择书写这些器物就是呈现他的观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很少被仔细凝视,《江南器物志》所讲述的,证是这个国家最多数人的生活历史,最漫长、最普通的,也是关乎日常劳作的历史。尽管像布老虎鞋、街边酒坊的酒瓶这类器物,既不能进入传统文物研究的视野,也很难被奉于博物馆,更不能登上拍卖场的舞台成为财富的符号,但它们与普通人的悲欢喜乐连在一起,凝聚了人的情感、劳动、智慧、创造、挫折、苦痛。
对江南的文学性、历史性书写自古有之,这逐渐让江南成为一个“文人化”、狭窄化的江南。而《江南器物志》中的“江南”不是文人的,它是民间的,是广大默默无闻老百姓的民间。它包含了老百姓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细小琐碎,却也惊天动地。这个“江南”才是生活的江南,才是中国人生活图景的本来面貌。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关于江南文化与生活日常的抢救性整理与阐释。
人与器的相互成全——写作的审美也是生活的审美
“器有骨骼,物有灵性。”通过《江南器物志》,程永新看到了徐风写作新的可能性,也看到了历史与我们当下生活之间的新关系。器物投射了人的情感、历史、审美和品质,也由此展现了江南地区的经济活动、情感活动、审美活动——一块在江南版图上如邮票大小的“器隐镇”,是江南人生活方式的浓缩。这座古镇充满了亲和力,与大城市中人与人交往的陌生感不同。江南人即便在生意场上,也会流露出一种含蓄、艺术和审美;即便在最普通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中,也懂得“敬物惜福”的生活之道。
程永新说,器物的命运也就是人的命运,是人的灵魂的投射,徐风的文笔与江南人的生活一样美而动情。他通过一个个器物把一段段历史呈现出来,又把世道人心展现出来。他写一张合欢桌,丈夫远行未归,合欢桌的一半就在家中被妻子藏起;多年后丈夫成立另外的家庭,合欢桌的一半也无可奈何地流散江湖——器物在江南生活中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半张桌子就把一个女人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也把她的心酸道尽”,徐风说,“我依稀感觉到有一个女子在朝我缓缓走来。有了这样一张桌子,有了它在江湖上辗转一百多年的意识和经历,我觉得这个‘女子’就在岁月深处看着我,我用文笔把‘她’写出来,使她与现实有一种勾连。”
书中也写到一颗夜明珠,被安放在早逝的丈夫口中,寄托深情与念想,却在乱世中被掘墓人偷走;偷走夜明珠的正是家中的长工,女主人在乱世中历经沧桑,却最终淡然地宽宥了他们——器物既讲述生活历史,也传达世道人心、慈悲风华。器物,更塑造了人的样貌。
正如主持人秦忆所总结的,这本书虽然叫《江南器物志》,但是它绝对不仅写器物,而是写人如何造器,器如何渡人,人与器的相互成全。文化并不是悬浮在空气中的虚影,而是千百年来承载在我们所用的器物中,扎根于我们生活的土壤里,更是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正如作家本人所说:“我想记叙头顶的明月,我想探究脚下的厚土;我想追述祖辈们铭刻在器物上的恩德,我想解析时代差异留在器物上的胎记。”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今天,通过书写、阅读、探讨这些浸润着江南水土气息的器物故事,我们将共同完成文化与历史的传承与对话。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