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什么叫“灵魂在工作”?《灵魂在工作:从异化到自主》一书的作者认为,灵魂是人类存在的领域,涉及语言、创造力和情感,而在当下的数字时代,思维、语言和人类情感已成为资本剥削人们的核心领域,我们正处于一种工作的新异化……
本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为了理解过去几十年社会对劳动的看法经历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如何决定了工人在文化和心理上对劳动的依赖状况,我们既需要分析信息生产领域内欲望的投资,也需要分析劳动关系的形式。
数字转型启动了两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过程。第一个是将工作捕获进网络内,即通过数字基础设施使不同劳动片段协调成独特的信息和生产流程。第二个是将劳动过程分散到形式上自主,但实际上相互协调并最终相互依存的众多生产岛屿中。如前所言,认知劳动表现为信息劳动,即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的无数信息的无限重组。当合作意味着转移、加工和解码数字化信息时,很明显网络是其自然框架。
指挥的功能不再是一种位于工厂中的等级制强加,而是一种横向的、非地域化的功能,渗透到劳动时间的每个片段中。
网络通信的非等级制特性在整个社会劳动周期中变得占主导地位。这有助于将信息劳动表现为一种独立的工作形式。但正如我们所见,这种独立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虚构,掩盖了一种新的、日渐增长的依赖形式,尽管不再是以前的形式等级制度(对生产行动的指挥是直接和自愿的)。这种新的依赖性在网络的自动流动性中越来越明显:我们的主观(劳动)片段严密地相互依存,所有这些片段都是不同的,但在客观上依赖于一个流动的过程,依赖于一系列自动化机制,这些机制既外在于又内在于劳动过程,调节着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生产片段。
无论是只执行任务的工人,还是企业经理,都清楚地感觉到他们依赖于不能中断、不能退后一步的持续流动,除非冒着边缘化的风险。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不再由泰勒主义工厂典型的大小领导层级制度保证,而是纳入流动中。手机可能是最好地说明了这种网络依赖性的技术设备。即使在不工作时,大多数信息工作者也会一直开着手机。手机在组织劳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此时劳动者作为一种自我企业,形式上是自主的,但实际上是具有依赖性的。数字网络是实现劳动的空间和时间全球化的领域。全球劳动是无数片段的无尽重组,这些片段生产、加工、分发和解码各种类型的符号和信息单元。劳动是网状活动,在这种活动中,网络激活了无尽的重组。手机是使这种重组成为可能的工具。每个信息工作者都有能力加工一个特定的符号片段,这个片段必须与无数其他符号片段相遇并匹配,以组成一个组合实体的框架,即信息商品或符号资本。
但为了使这种组合成为可能,一个单一的、无限灵活的(并且不断地对符号资本的呼唤做出反应的)生产片段是不够的:需要一个设备,能够连接单个片段,不断地协调和实时定位信息生产的片段。手机作为过去十年最重要的消费品,在大众层面提供了这个功能。如果工业工人想通过在特定区域反复执行生产动作来换取工资,他们必须每天在特定的地方度过八个小时。
产品的运动性是通过流水线实现的,而工人则必须在空间和时间上保持不动。相反,信息工作者不断地在网络空间的长度、宽度和深度中移动。他们移动是为了寻找符号,加工经验,或者仅仅追随他们人生的道路。但在每一个时刻和地方,他们都是可以联系到的,可以被召回以执行特定的生产功能,重新插入全球生产周期中。在某种意义上,手机实现了资本的梦想:在生产周期需要它的确切时刻,吸收尽可能多的时间原子。以此方式,工人把整天都献给了资本,但只有网络化的时间才收费。信息生产者可以被视为神经工作者。他们时刻做好准备,尽可能长时间地将他们的神经系统作为一个活跃的接收终端。一整天的生活都受制于符号激活,只在必要时才直接产生生产力。
但是,我们长期遭受认知的永久性电击所带来的持续压力,这意味着怎样的情感、心理和存在代价?
幸福不是科学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这才是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
即使在公共话语中无法找到基于科学且连贯的关于幸福的论述,我们依然能看到建立在幸福的观念上的完整交流。我们见证了碎片化和虚构的诉求在流传,这些诉求很少是合理或连贯的,但仍然极其有效。在20世纪90年代,当生产过程变得非物质化时,主要的修辞都集中在幸福上:幸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几乎是强制性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遵循某些行为规则和行为方式。
无论是极权主义政治话语,还是民主政治话语,都将幸福置于集体行动的视野中。极权主义实施强制性的行为程序,要求公民热情接受,否则他们将被边缘化和迫害:谁不快乐,谁就不爱国。
民主并不期望狂热的集体认同。相反,从成熟的角度来看,我们将民主视为一种不懈的追求,旨在达成一种可能的共处之道,使个人能够认同那些能够带来相对幸福感的个人行为和公共行为。
资本主义经常(毫无理由)地被描述为民主不可分割的伴侣(尽管我们知道它经常在远离民主政权的阴影下繁生),但实际上它根本不宽容。因为它期望热情参与普遍的竞争,然而在竞争中,如果没有充分而令人信服地部署我们所有的能量,是不可能获胜的。
极权主义政权,像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威权国家,以集体和同质化的幸福为名,剥夺了人民的自由,从而产生了无尽的悲伤。
但即使是自由经济,随着广告话语以夸张但有说服力的方式表现对利润和成功的崇拜,最终也产生了由不断的竞争、失败和罪恶感引起的不幸福。
在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理念声称,自由市场游戏为人类创造了最大的幸福。事实上,新经济的一个效果是意识形态和广告信息的同化,以及将广告转变为经济理论和政治行动的某种范式。
众所周知,广告的话语基于创造虚构的幸福模式,并邀请消费者复制这些模式。广告系统性地生产幻觉,因此也系统性地生产幻灭、竞争、失败、欣快和抑郁。广告的交流机制基于产生一种匮乏感,引诱人们成为消费者,以便感到满足,最终获得一直逃避我们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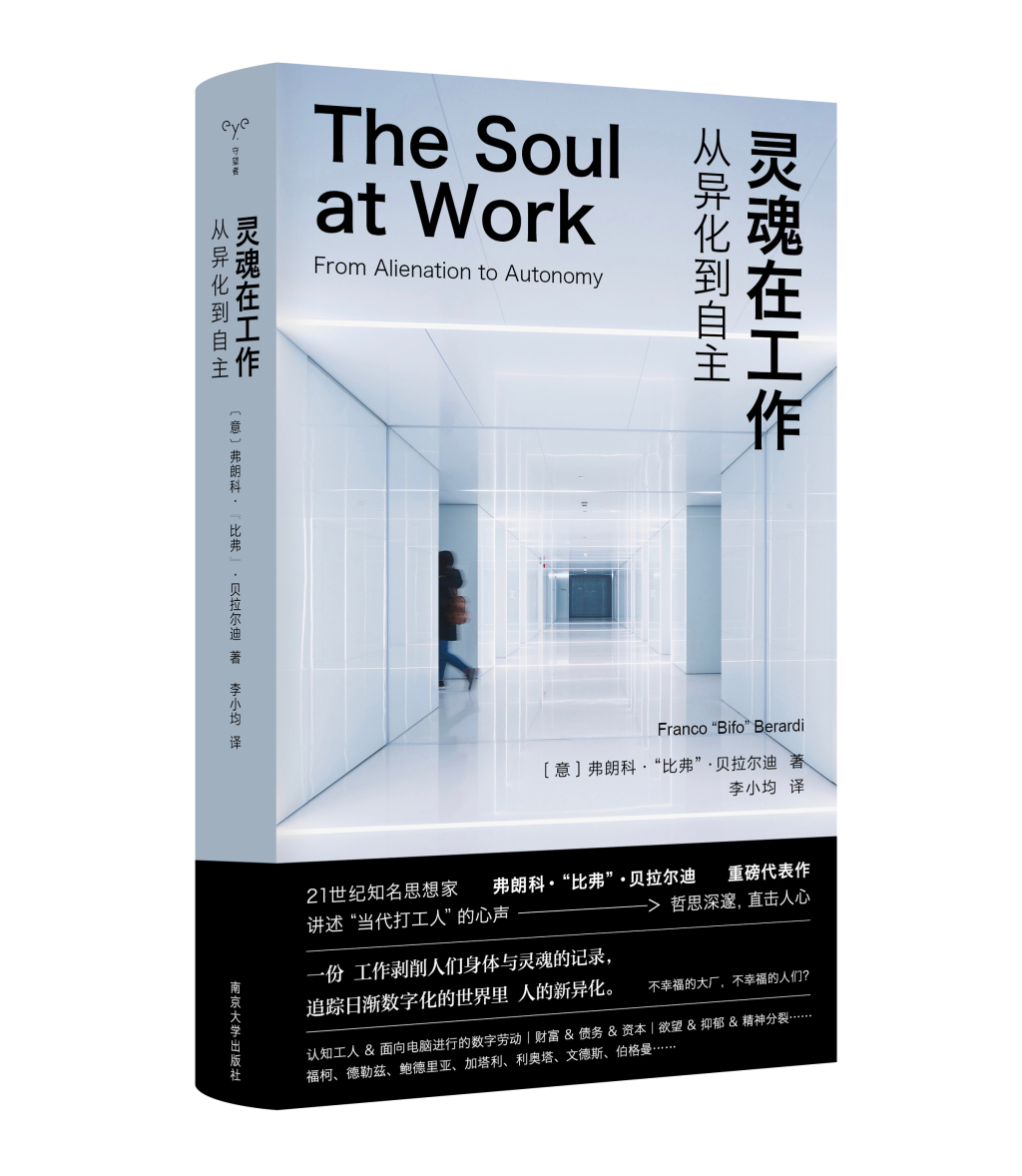
《灵魂在工作:从异化到自主》,[意]弗朗科·“比弗”·贝拉尔迪著,李小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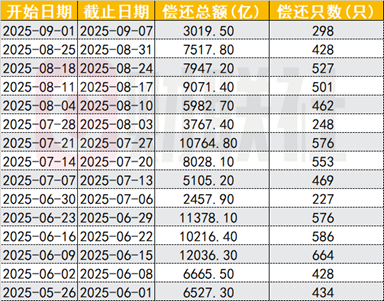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