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游者:西方宇宙观念的变迁》,[英]阿瑟·库斯勒著,莫昕译,后浪|九州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568页,128.00元
1997年,法国肌肉萎缩治疗协会开展了一项特别行动。他们召集了一个病人群体,通过一档电视慈善节目募集到了八千万美元慈善基金。由于导致肌肉萎缩的疾病其病因往往在于基因,因而这笔善款一度被大量用于人类基因组的基础性研究。然而在相关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之后,该基金却解散了用于进行基础性研究的实验室,转而倾其全力投入到对病人们而言更迫切,但对于当时科学而言过于超前的基因治疗领域当中。
在拉图尔看来,这一事件体现了在当今世界,科学研究早已脱离了孤立的“实验室生活”,进入开放性的“集体实验”状态,被社会因素影响,同时也左右人们的生活。然而这种“集体实验”并不意味着科学有效地介入了社会,能够为其理清秩序、终结争论,反而在社会语境中增加了更多新实体。“在那些代表了人类及其需求的代言人之外,他们新加入了那些代表了——我该如何称呼之呢?——非人类及其需求的代言人……现在,只有一件比死亡和税收更加确定的事情,那就是,相比过去而言,将来会有更多此类奇怪的野兽”([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刘鹏、安涅思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7月,xviii-xix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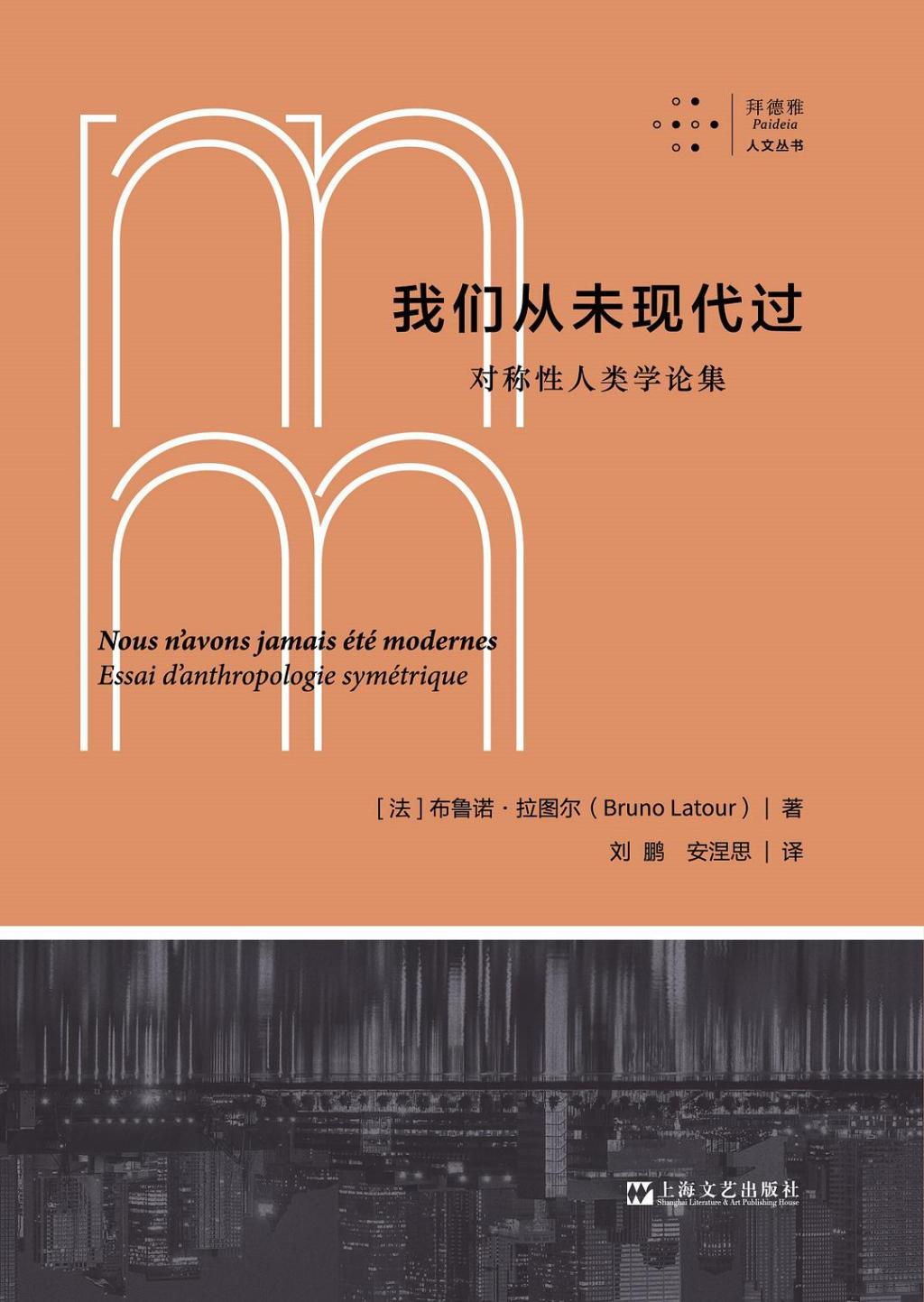
拉图尔著《我们从未现代过》
拉图尔进一步指出,这种混乱状态的出现,根源在于尽管科学已经极大程度地与社会纠缠在一起,但人们依然倾向于将科学视为一种理想之物,期待它仅凭自身便可以发现乃至于“发明”一种救赎之道。将科学视为一种孤立且至高理想的信念——拉图尔干脆将这种信念称为由科学革命开启的“潘多拉之盒”——离不开对科学发展的辉格史叙事。既然我们相信是哥白尼赋予了太阳宇宙中心的地位,以及伽利略曾经如大卫一般独自挑战并击败了旧时代的巨人亚里士多德,我们便很难不把科学当成一种“神话”,相信它可以拯救世间一切,甚至包括我们的灵魂——于是科学真正享有了与中世纪教会同等的地位。
实际上,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阿瑟·库斯勒便已经看到了这种现代性危机。在首版出版于1959年的《梦游者》一书中,库斯勒旨在强调人们眼中的科学英雄——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绝非人们普遍想象的那般自觉且坚定,“一些最重要的个人发现到来的方式令人觉得更像是一位梦游者而非一台电脑的表现”(第ix页),于是科学发展“走的是一条曲折的之字形路线,有时几乎比政治思想的演变更令人困惑”(同上)。作为一位小说家,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恐怖政治”的亲历者,库斯勒这项科学史研究的根本意义在于取消科学与社会的隔离状态:科学工作始于也始终都在“拯救现象”,正如社会发展的意义在于个体的更好生活——决定其地位的只能是现象与个体的无限性,而非仅凭一项“绝对进步、绝对正确”的事业便能终结一切的妄想。
既扭曲又分裂的人性之材
不难想见,库斯勒此书争议颇大。尽管他对科学史“曲折前进”的描述比托马斯·库恩著名的“范式转换”更早提出,但科学界对这部作品很难买账。美国天文学家、科学史专家欧文·金格里奇专门写了一本《无人读过的书》,试图通过追踪早期版本《天体运行论》拷贝在世界各地的流转状况,驳斥库斯勒在描述哥白尼这部大作时使用的这个小标题。“当然,并不是所有这些拥有者都真正读过这本书。那些王室成员并不在他们的拷贝上做任何批注,但另外一些人这样做了……显然,当库斯勒断言《天体运行论》是‘一本没有人读过的书’和‘有史以来销量最差的书’的时候,他就犯了错误。他真的错了。大错特错。”([美]欧文·金格里:《无人读过的书》,王今、徐国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月,29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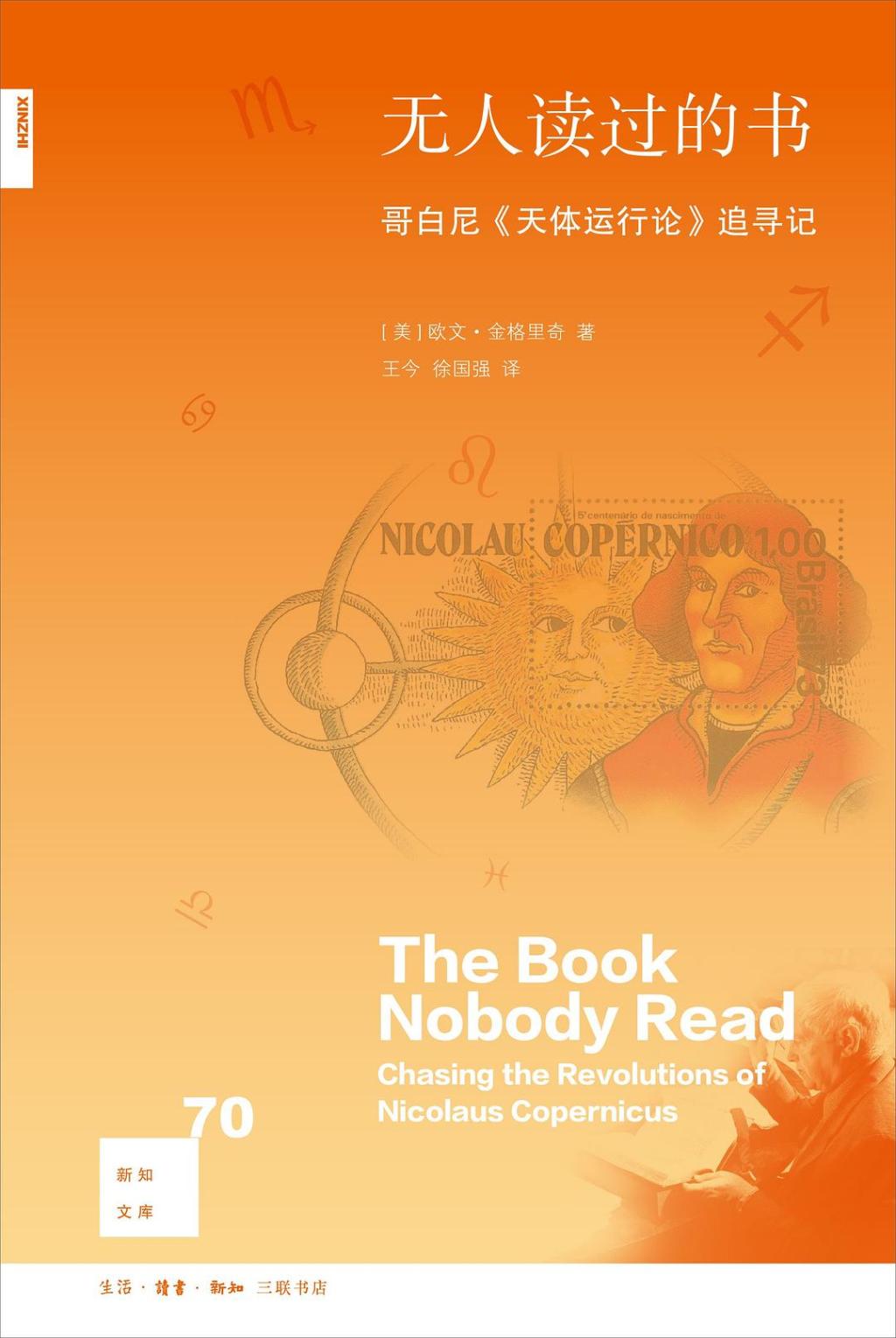
金格里著《无人读过的书》
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仅凭这段引用我们便不难感受到金格里奇对于捍卫他心目中科学英雄的热情。这种热情使得他的这本《无人读过的书》算得上是一本信息丰富的传播史佳作,但也正是这种热情,令他从一开始便误读了库斯勒的用意。库斯勒宣称《天体运行论》是一本“无人读过的书”自然言过其实,但他主要是为了强调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哥白尼的作品销量实在不佳。“它的第一版,纽伦堡1543年版,印数一千册,从来没有卖完。它在四百年里一共重印了四次……同时代其他天文学作品中,最畅销的是一个约克郡人约翰·荷里伍德写的教科书,不少于五十九个版本。耶稣会神父克里斯托弗·克拉维乌斯的《论天球》出版于1570年,在五十年里十九次重印……上述这些作品,在十六世纪末之前总共在德国重印了大约上百次,而《天体运行论》仅有一次。”(159页)
库斯勒讨论哥白尼著作的滞销,是为了强调这部作品极其难读,而这种阅读上的难度进一步体现在现代学者在讨论哥白尼原著时常常出现的纰漏,“与流行的看法,甚至与学术观点相悖的是,哥白尼并没有减少轮圈的数量,而是增加了。这个错误的观念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久,被这么多杰出的权威人士不断重复呢?答案是,极少有人读过哥白尼的书”(160页)。
自然,阅读难度不应成为一部学术作品不被阅读的根本原因。于是库斯勒进一步指出对于研究者,“哥白尼的系统(相对于日心说)几乎不值得关注”(同上),“哥白尼系统作为拯救现象的手段更具几何上的简洁性……(但)哥白尼的物理学观点纯粹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他的演绎方法也严格遵循着经院哲学的路线”(165页)。到这里,库斯勒已经对哥白尼科学英雄形象进行了基本解构:哥白尼绝不是纯粹的革新者乃至于革命者;相对于颠覆传统,他更倾向于基于传统“锦上添花”。
由此围绕哥白尼的生平与《天体运行论》发表的历史疑点,在这里便有了更合理的解释。我们知道在“离经叛道地”出版《天体运行论》之前,哥白尼始终是一位“忠诚”的教士。库斯勒注意到,除了这部作品,哥白尼还出版过一本翻译作品《塞摩卡塔书信集》。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哥白尼投身翻译事业的精明动机:
我们必须记住,这是一个精神上正在发酵,知识上正在革命的年代。若将哥白尼教士的品位和风格与他同时代的杰出人物伊拉斯谟等人比较,都会令人倍感沮丧。然而这项翻译工作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在这个时期,翻译重新发现的古希腊文本被认为是人文学者最首要和最崇高的一项任务……然而,在北欧,神职人员中更顽固的少数派仍在进行反对学古复兴的抵抗行动……这些考量可能有助于解释哥白尼为什么特别选择了这本书。它是希腊文的,因此在人文主义者的眼中翻译这本书值得称赞;但它不是一本古希腊的书,而是七世纪一位拜占庭基督徒写的,沉闷虔诚、无可指责,就连最狂热的修士也无法予以反对。(112-113页)
假如我们相信人格的统一性,哥白尼更为人熟知的事迹同样可以在这个“精明性格”的框架下得到解释:日心说是必要的,沿袭传统方法也是必要的,而最终选择发表《天体运行论》也并非蒙受真理的呼召,而仅仅是因为他等到了安全的时机。事实上,在哥白尼的年代,发表日心说的阻力并不在于教会(“我们必须记住,《天体运行论》在出版七十三年后才被列入《禁书目录》,而臭名昭著的伽利略审判要等到哥白尼去世九十年之后了。这一时期欧洲知识界大气候的变化……几乎相当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到希特勒-斯大林时代之间的变化。”[123页]),而在于同行压力。库斯勒在哥白尼的藏书中找到了一句被他特别标记的警句,似乎可以用来佐证这一点:“因为纯净的清水会被浪费而泥垢只是被稍稍激起。”(122页)
库斯勒的野心并不止于解构哥白尼其人,他更希望以哥白尼作为典型,探讨中世纪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他们怀有怎样的渴望,又受制于怎样的局限——当然不仅仅是普遍认为的教会专制。“日心说从未被遗忘……然而同时,宇宙学已经回归到了天真的原始形态的地心说……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天文学家们至少试图拯救现象,而中世纪的哲学家们却无视现象。但无视现实的话生活就过不下去了。因此分裂的心灵必须为它的两个不同的隔间发展出两种不同的思维规范:一个符合理论,另一个符合事实。”(79页)这种分裂现象既是中世纪知识分子普遍的思想状态,或许也代表了一种人性常态,如康德的名言“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分裂的心灵,自然也无法想象世界的和谐。
硕果累累的错误
然而也正是这种分裂,确保了哥白尼在其时代的安全无虞。既然一个稳定的知识大厦已然奠基,那么允许哥白尼这样一个“小数学家”(约翰·邓恩语)以假设之名在“真理”的外围敲敲打打又有何妨?但在库斯勒看来,正是通过这些起初不被人们重视的零敲碎打,哥白尼得以在科学革命中扮演关键的“结晶者”角色: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化学过程,可以说明我说的结晶者是什么意思。把厨房用盐放入一杯水中,待水“饱和”,无法再溶解更多的盐,此时把一根打结的线悬垂在溶液中,经过一段时间后,在线头打结处会形成晶体。线结的形状和纹理与是否结晶并不相关;重要的是溶液已经达到饱和点,一旦提供一个核心,围绕核心就会开始结晶。中世纪末的宇宙学已经溶入了地球旋转和运动的模糊概念,加上毕达哥拉斯学派、阿里斯塔克斯和赫拉克利德斯、马克罗比乌斯和普林尼的回应,以及库萨和雷吉奥蒙塔努斯投入的令人激动的论述,已经达到了饱和点。哥白尼教士正是耐心的线结,他悬浮在溶液之中,使其得以结晶。(176页)
哥白尼这位“结晶者”凝结的第一块重要“晶体”便是开普勒。尽管库斯勒对开普勒赞赏有加,但他重构的开普勒形象依然无法令现代科学主义者感到满意,因为在他笔下,比起“科学精神”,开普勒似乎更醉心于神秘主义。“还在孩提时代,他就对过去的自己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自己的样子这个问题感到着迷……现代人对此有成套的解释,包括染色体和基因、适应性反应和创伤经历等;而十六世纪的人只能从宇宙整体在他受孕或出生那一刻由地球、行星和恒星星座所呈现的状态中寻求解释。”(207页)更冒犯的是,库斯勒认为开普勒重要的实证主义精神——譬如因为其当时理论与实际观测仅仅相差八弧分便抛弃最初的理论,进而为行星“更换”了椭圆轨道——并非源于当时的航海业与工商业发展倒逼更精确的科学成果,而是“由于他把物理学的因果律引入到天空的形式几何学中”(281页)。库斯勒宁愿相信比起经济现实,开普勒更忠诚于灵魂的和谐,这在今日研究者看来缺乏“实证”,但或许更接近历史人物的“通性真实”。
库斯勒对开普勒的论述,另一争议点是在他看来,开普勒在研究中常常犯错,却又总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这全凭“运气加直觉”(290页)——“一个用弯曲的粗铁丝打开复杂锁具的锁匠不是受逻辑的指导,而是受无数过去关于锁的经验的无意识残留的引导……也许正是这种断断续续地闪现的整体视野,可以解释开普勒前后犯下的错误的相互抵抗”(292页)。不过在我们已经看到所谓理性也并不能必然保持正确的情况下,库斯勒至少没有夸大开普勒的直觉所取得的成绩,“如果开普勒没有进入物理学领域,那他就不可能获得成功……(开普勒的物理学)是一种处于亚里士多德与牛顿之间的‘分水岭上的物理学’……他离发现万有引力已经很近了,而他却未能发现”(293页)。
但开普勒已经走得足够远——远到超越了哥白尼的零敲碎打,使教会的宇宙学大厦感受到了来自这些“小数学家”的震动。这里有一段经常被科学史家忽略但被库斯勒捕捉到的插曲,即在开普勒提出前两条行星运动定律与第三定律之间,他的母亲遭遇了“女巫审判”,这位“丑陋的小老太太”仅仅是因为性情乖戾、好与人争执,便遭到检举,经历了长达十四个月的漫长监禁与审判(其中一条罪名“被告在听到《圣经》中的训诫时没有流泪”[342页]不免让人想起日后加缪笔下的默尔索那条经典罪状)。尽管她最终通过了“酷刑试炼”,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但还是在被释放六个月后撒手人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普勒撰写了《世界的和谐》。在这本书中,他将行星的第三定律送给了他可爱的同时代人。”(343页)“他从年轻时就一直在寻找这个第三定律,也就是寻找行星周期与它的距离之间的关系。没有这种相关性,宇宙对他来说就毫无逻辑。它就是一个随意的结构。”(349页)尽管无从把握自己生命的结构,更无力改变“可爱的同时代人”的愚妄,但开普勒还是成功地将宇宙与人类头脑中的科学原理融为一体——到开普勒这里,西方世界方才自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被驱逐以来,再一次找回构建和谐世界的可能。
“语法虚构”与“海洋感觉”
我们当然不能忽视作为写作者的库斯勒,其最主要的成就还是通过作为小说家取得的。于是他在《梦游者》中着力构建的三位科学家形象,其实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文学色彩,而开普勒身上的“主角光环”尤为明显。事实上,如果库斯勒只写一本开普勒的传记,或许在观感与文本结构上会更加平衡。
但再一次,库斯勒的野心使他绝不会安于写作一本科学家传记。当他有意或“梦游”地将开普勒塑造为超然于世的主角,便意味着剩下的两个角色既是必要的“陪衬人”(左拉语),又是更普遍存在的形象,正如他在其小说代表作《中午的黑暗》中的安排:你不可能指望悲剧英雄鲁巴肖夫时常出现,但在极权状态下,愚蠢的投机者格列金和犬儒的同情者伊凡诺夫都是可被“批量生产”的存在。
所以伽利略被“分配”到的角色是伊凡诺夫吗?的确,犬儒式的自作聪明使得他更容易冒犯到愚蠢的投机者,正是这一点为他招来了宗教审判的麻烦。但如果说伽利略仅仅是科学精神的同情者,显然有失公允。于是在库斯勒笔下,伽利略的创新精神首先得到了肯定——正是这种创新精神为他招来了麻烦,“有一群强大的敌人,他们对伽利略的敌意从来就没有消退过,那就是大学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们。人类思维的惯性和对创新的抗拒,最清楚地表现在了那些在传统中拥有既得利益并垄断了知识的专业人士身上”(379页)。但他还是忍不住强调这位科学英雄的人格缺陷。伽利略过于好斗的性格使他并无必要地树敌无数,“其他伟大的科学家,包括牛顿,也曾卷入过充满敌意的争辩。但这些相对于他们的工作而言都是次要的……伽利略悲剧的特殊性在于,他的两本主要著作都是在他七十岁之后才发表的……他一生的黄金时代都消耗在这些小打小闹中了”(419页)。而在库斯勒看来,伽利略性格的悲剧后果甚至不仅限于他个人,当他一意孤行为日心说辩护,甚至不惜扭曲哥白尼的本意,那场臭名昭著的伽利略审判的后果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对自由精神的戕害更为深远,“正是伽利略考虑不周的斗争败坏了日心说系统的名声,促成了科学与信仰的分离”(441页)。
实际上,库斯勒对于伽利略审判的独到见解,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法国理论物理学家皮埃尔·迪昂发表于上世纪初的一系列科学史论文的启发,但迪昂的结论要比库斯勒更乐观也更“科学”:
当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异口同声地宣布,天文学应该只把被物理学确立为真的命题作为它的假设,这个独具慧眼的断言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它可以被认为,天文学假设是对天上事物的性质及其实际运动的判断。它也可以表示,实验方法通过充当对天文学假设正确性的把握,将以新的真理来丰富我们的宇宙学知识。可以说,第一种含义停留在断言的表层,它是直接显现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伟大天文学家清楚地看到了这层含义,他们对此做出了正式的表达,也正是这层含义赢得了他们的效忠。然而如果这样理解,他们的论点是错误且有害的。([法]皮埃尔·迪昂:《拯救现象》,庞晓光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5月,18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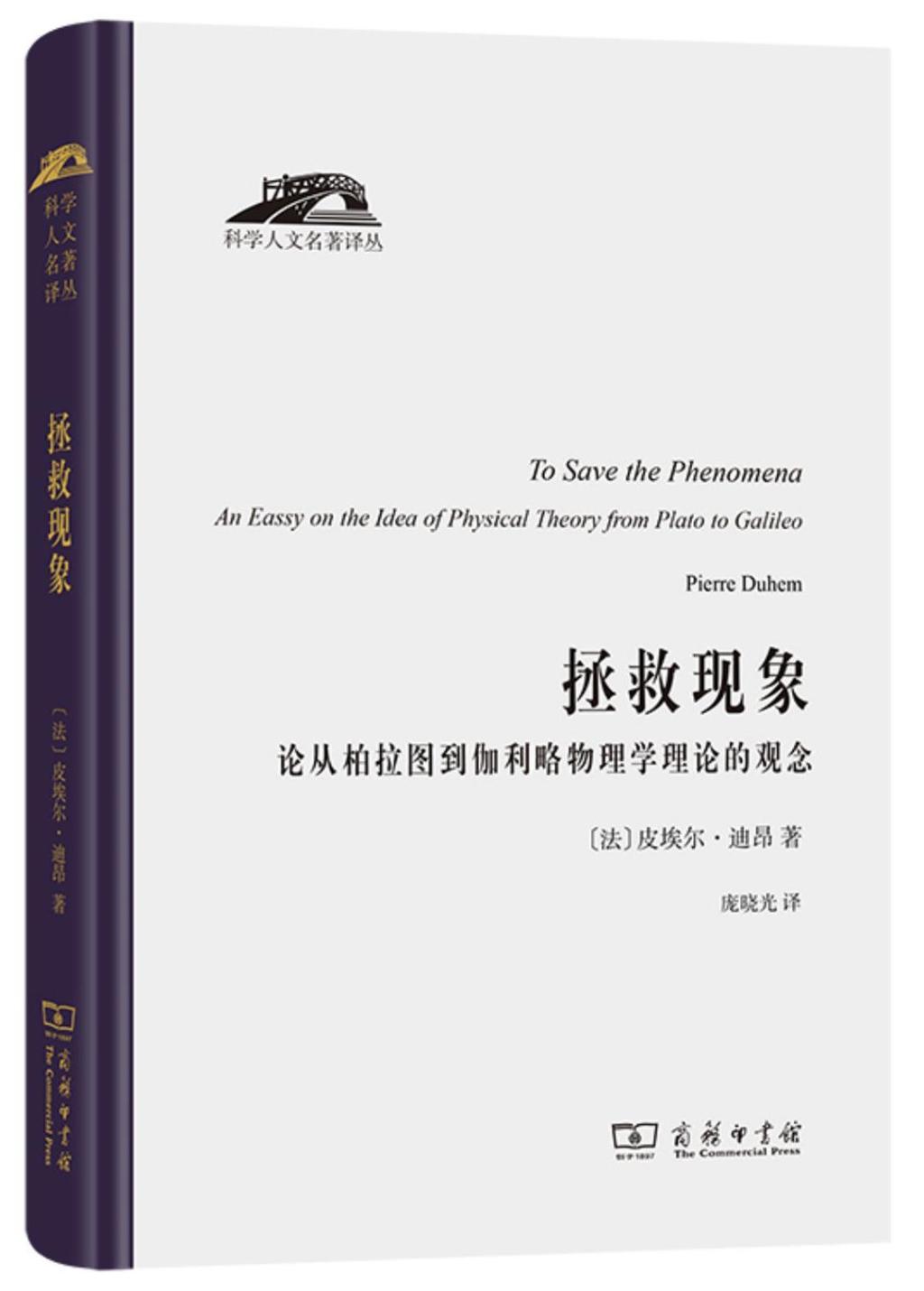
迪昂著《拯救现象》
简言之,在迪昂看来,基于当时的是非准则与科学进展,宗教法庭判定伽利略的主张错误无可厚非;同时对于这一判决结果,迪昂看到了其积极的一面,“尽管有开普勒和伽利略,但我们今天与奥西安德尔和贝拉明一样认为,物理学假设仅仅是为了拯救现象而设计的数学发明。但是,幸亏有开普勒和伽利略,我们现在要求他们把无生命的宇宙的所有现象一并拯救”(同上,185页)。
二十世纪初的迪昂仍在期待现代科学兑现其拯救所有现象的潜能,但半个世纪后的库斯勒已经不再相信科学仅凭一己之力便能实现这一点,于是对伽利略代表科学对信仰直接宣战痛心疾首;同时库斯勒还在忧心人类心灵再次分裂的长期后果:“一个被神操纵的傀儡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一个由染色体操纵的傀儡只是怪诞可笑而已。”(482页)库斯勒的担忧,到二十世纪末已经非常接近于现实,如法国哲学家勒内·基拉尔在1996年进一步做出的预言,“在人文主义信奉的‘信条’中,有基因操纵……最多几十年后,我们就会把人转变成一台台恶心的享乐机器”([法]勒内·基拉尔:《欲望的先知》,钱佳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164页)。而随着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所谓“生物世纪”,这里的“生物”究竟指向曲折前进的科学,还是降格的神学信仰,将会决定“人类世”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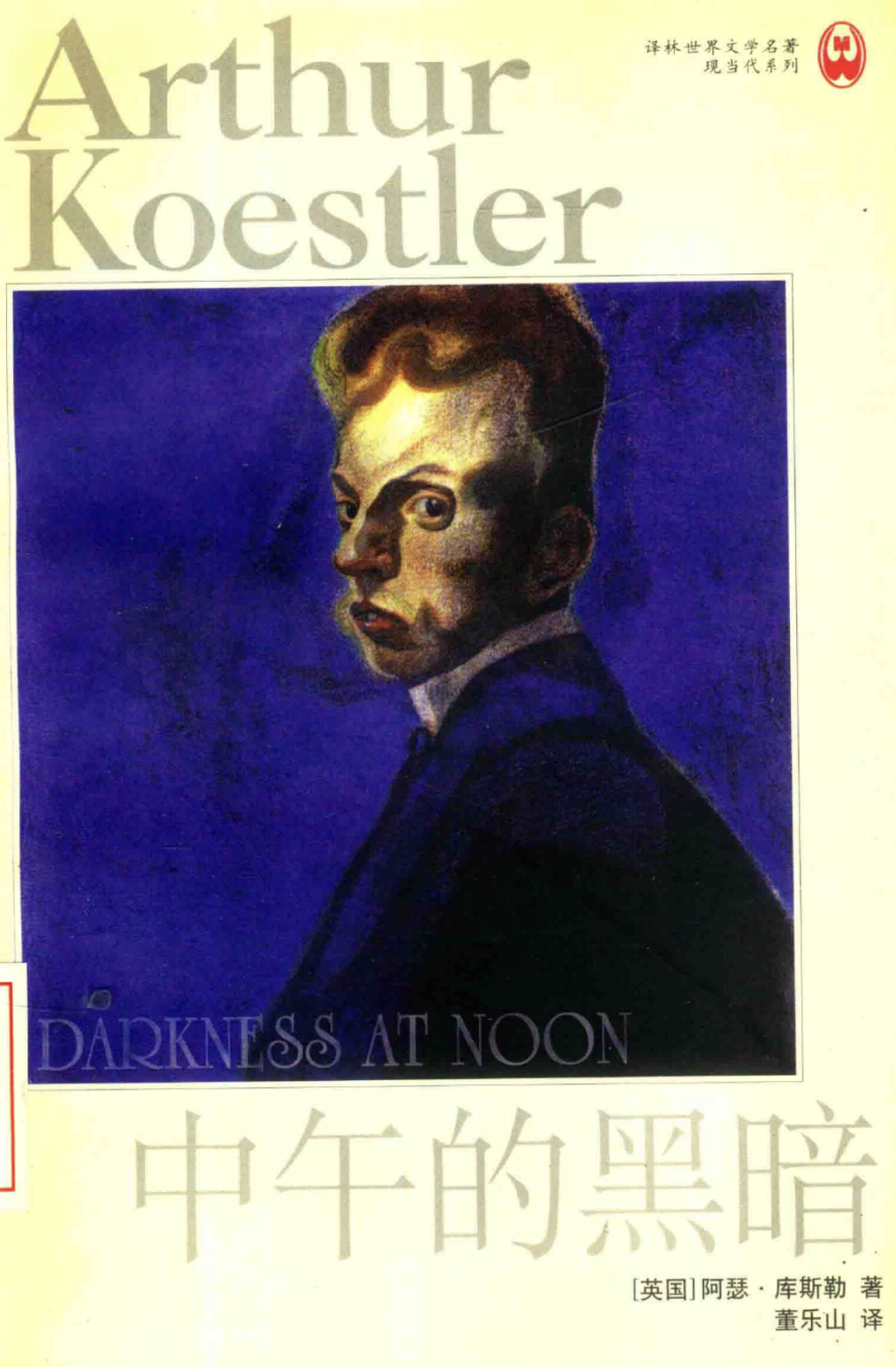
库斯勒著《中午的黑暗》
在小说《中午的黑暗》里,库斯勒的悲剧英雄鲁巴肖夫出于“纪律要求”,对自我意识感到羞耻,只能借用维特根斯坦的术语,将脑中的“我”视为“语法虚构”;到小说结尾,鲁巴肖夫即将面临死刑,他回想自己“为信念工作”的一生,感到身心俱疲,甚至连那个语法虚构的“我”都无力召唤。“但是还有途径可以接近他……最伟大和最清醒的现代心理学家承认这种状态是事实,称它为‘海洋感觉’。的确,一个人的性格就像一粒盐一样溶解了,但同时,无限的海洋似乎包含在这粒盐中”([英]阿瑟·库斯勒:《中午的黑暗》,董乐山 译,作家出版社,1988年11月,274页),接着他想起自己儿时的理想,“小时候他曾真的想学天文学,可是后来四十年他却在干别的。公共检察官为什么不问他:‘鲁巴肖夫被告,谈谈无限怎么样?’”(同上,275页)。或许这便是库斯勒撰写这部关于伟大天文学家之“盐”以及天文学之“海”的《梦游者》,以及他后半生投身神秘主义研究的根本原因。“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咸是现象,亦是灵魂——一粒包含无限海洋的盐足以将其拯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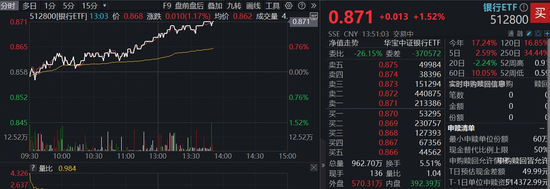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