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璀璨结晶,承载着人们生活的点滴、工作的奋斗与梦想的追逐,其演变轨迹、发展规律与内在运行逻辑,始终是社会科学领域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从经济学视角审视,诸多现实困惑亟待解答:为何有的城市生产率远超其他城市?城市兴起与衰落的根源是什么?为何部分地区房价居高不下?这些看似独立却又紧密关联的疑问,共同勾勒出城市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人们为何聚居在城市?在众多探索城市奥秘的学科中,经济学凭借其独特的分析框架与理论工具,为我们理解城市的本质、功能与发展趋势,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视角与思路。

一个“天才”的城市经济学家
城市经济学作为应对20世纪中叶美国城市化危机的学科应运而生,爱德华·格莱泽以其开创性研究重塑了该领域的理论范式。这位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身兼美国国家科学院、艺术与科学院等四院院士,荣膺社会科学领域最高荣誉Albert O. Hirschman奖,并于2023年摘得“引文桂冠奖”,其学术影响力可见一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群体也对其推崇备至: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称赞格莱泽是“天才”;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更强调,“格莱泽以全新方法论激活了濒临僵化的城市经济学。”
格莱泽的学术基因根植于1970年代在纽约生活的双重体验——既有第五大道的璀璨灯火,也有时代广场的犯罪阴霾;既目睹中央公园的文化交融,也亲历财政危机下的城市衰败。这种矛盾共生体激发了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终极追问:为何有的城市持续繁荣,有的却陷入困境?
经过大量实证研究,他坚信城市是创新与经济活动的核心引擎,能创造丰富机遇,认为“人类是通过与其他聪明人互动而变得更聪明的社会物种”。这一观点强调了城市中人际互动对知识传播、创新及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这种独特视角贯穿其代表作《城市的胜利》,书中以跨学科论证揭示——城市通过促进思想碰撞、降低创新成本,持续创造着知识经济时代的“集聚红利”。在本书中分析19世纪纽约制糖业的集聚现象时,格莱泽通过构建贸易成本与产业布局模型,证明城市因天然港口优势形成“运输成本洼地”,吸引制糖企业集聚,既减少分散建厂的重复投资,又通过劳动力技能共享推动技术改良。这一案例将地理优势与产业组织理论结合,揭示了城市通过降低要素流通成本激活集聚经济的微观机制。
一把真正理解城市的钥匙
城市经济系统复杂多样,涉及众多变量与因素,它们相互交织、彼此影响,数学建模是打开城市复杂经济现象大门的关键钥匙。格拉泽直接指出,“缺乏经济学工具,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城市;同样,不借鉴其他学科方法和研究成果,经济学家也不能真正理解城市。”数学建模通过构建简化且精确的框架,梳理和量化这些复杂关系,从而使我们得以洞察城市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
《城市、集聚与空间均衡》就是格莱泽教授关于城市经济学工具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在书中着重指出,理解城市经济学的关键在于把握不同决策主体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而数学模型为这种理解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空间均衡和集聚经济两个模型,被视为理解城市经济的核心理论基础。
一是空间均衡模型,解析城市内部与城市间的关系。城市经济学有两大经典空间均衡模型。描述城市内部的Alonso-Muth-Mills模型和描述多个城市的Rosen-Roback模型。前者假定收入不变,探究住房成本是否被交通成本所抵消;后者分析不同城市间收入、城市公共服务和住房成本的权衡取舍。以城市内部空间均衡为例,它涉及居民、企业和开发商等多个决策主体,这些主体在城市空间内的选择受工资、物价、交通成本、住房成本等多种因素影响。若仅依靠文字描述和定性分析,难以精准把握这些因素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它们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共同作用机制。而数学建模将这些因素纳入统一框架,通过严谨逻辑推导和数学运算,得出城市空间均衡的精确结论,如居民最优区位选择、城市规模与形态等。
二是集聚经济模型,阐释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集聚经济是城市经济学的重要主题,其理论揭示了个体因邻近其他个体而提高生产率的现象。这一理论为城市的存在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原理,解释了城市为何能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从降低运输成本的角度来看,克鲁格曼式的集聚模型表明,企业和消费者在空间上的集中可以减少货物、人员和思想的运输成本,从而提高效率。例如,在一个城市中,企业之间的地理邻近性便于原材料的获取和产品的配送,降低了运输成本,同时也促进了知识和信息的交流,有利于创新的产生。劳动力市场蓄水池模型则强调了大城市在应对生产率冲击时的优势,企业和工人在大城市中的集聚使得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工人能够更迅速地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提高了整个城市的生产力。
如何重塑对城市的理解
本书围绕城市研究的核心概念、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展开全面而深入地探讨,系统剖析城市的形成、发展、问题及相关公共政策,为读者呈现城市经济学的完整图景,也深化和重塑了我们对城市的理解。
一是深入理解城市现象的复杂性。全球大量人口聚集于城市地区,如2008年前后美国有2.2亿人集中在仅占国土面积4%的城市区域,东京、大孟买、上海等城市也是人口大规模密集。这种集聚现象引发格莱泽深入思考城市存在的意义,而理解城市集聚现象是解答城市经济学首要问题——城市存在原因的关键。格莱泽期望通过城市经济学研究,深入解析人们选择聚居城市的原因,以及城市如何改变人们生活,从而揭示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格莱泽认识到理解城市需综合考量这些因素,城市经济学为梳理这些复杂关系提供框架,有助于全面理解城市现象。
二是整合与传承城市经济学理论。城市经济学领域战后发展迅速,涌现出众多重要理论和研究成果。格莱泽旨在通过本书整合自身对城市经济学的理解,系统梳理相关理论和模型,为读者呈现清晰的理论框架。书中涵盖城市经济学基本概念如空间均衡、集聚经济,以及具体模型如Alonso-Muth-Mills模型、Rosen-Roback模型等,并介绍不同时期学者的研究贡献,帮助读者全面掌握该领域知识体系。格莱泽深受城市经济学领域先驱和学者影响,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亚当・斯密、冯・杜能等早期先驱,以及WilliamAlonso、RichardMuth、EdwinMills、JohnMeyer、JohnKain等战后杰出人物。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集聚经济的来源有着深刻见解,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限制”的观点为理解城市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视角,冯・杜能的《孤立国》是城市理论的开创性著作。WilliamAlonso的《区位与土地利用》建立了空间均衡模型,RichardMuth在住房和建筑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EdwinMills的研究涵盖城市内部经济活动区位等多个方面,JohnMeyer推动了交通经济学与城市研究的结合,JohnKain在城市问题尤其是种族相关问题的经济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贡献。格莱泽在借鉴前人研究基础上,融入自身思考和成果,传承并拓展这些知识,为后续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参考。例如,书中对AMM模型的详细阐述,既传承前人成果,又通过展示模型变体和应用加以拓展,通过对模型假设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在不同情境下模型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为读者提供了更全面的理解。
三是助力城市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格莱泽认为城市经济学研究需基于合理的理论模型,但当前该领域研究存在部分问题,如部分研究对理论模型运用不足,或在实证研究中未正确考虑空间均衡等重要概念。格莱泽希望通过本书提供一系列实用模型,如城市内部和城市间的空间均衡模型、集聚经济模型等,为学术研究夯实理论基础。格莱泽坚信经济学方法可改善地方决策,因此书中不仅探讨理论模型,还涉及城市与政府关系,包括政府政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及城市经济学如何为合理城市政策提供支持。例如,书中对土地利用政策、地方再分配政策、最优税收政策等的讨论,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理论依据,助力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政策,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结语:理论的时代重构与地域转译
在全球化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语境下,格莱泽的城市经济学理论需要从西方学术范式到数字文明时代下中国实践场景的系统性“转译”。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转译,既有助于回应数字文明时代城市发展的共性命题,也有助于为中国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特色的理论解决方案。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格莱泽的理论提供了一套“城市治理的经济学语法”,技术赋能推动城市经济学研究范式从“事后解释”向“事前预测”转型。值得关注的是,格莱泽强调“制度僵化对城市活力的扼杀”——无论是过度管制土地供应导致的房价高企,还是行政壁垒阻碍的要素流动,均可能使城市陷入“规模不经济”困境。这一警示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具有现实意义,提醒政策制定者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寻找动态平衡。
2025年,站在数智时代的门槛边眺望,格莱泽的城市经济理论可以超越学术范畴,成为理解现代化城市文明的理论工具。正如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作为跨越时空的回应,《城市、集聚与空间均衡》的终极意义可能就是,在数字技术重构城市肌理的时代,每个城市研究者与实践者如何在集聚红利与空间均衡的资源配置博弈间,以及短期增长效率与长期可持续性的发展悖论间,探究构建更具张力的平衡机制,以趋近“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本质诉求。
这或许就是城市经济学的终极魅力:用理论洞悉底层逻辑,以创新塑造美好城市。
(本文系《城市、集聚与空间均衡》的导读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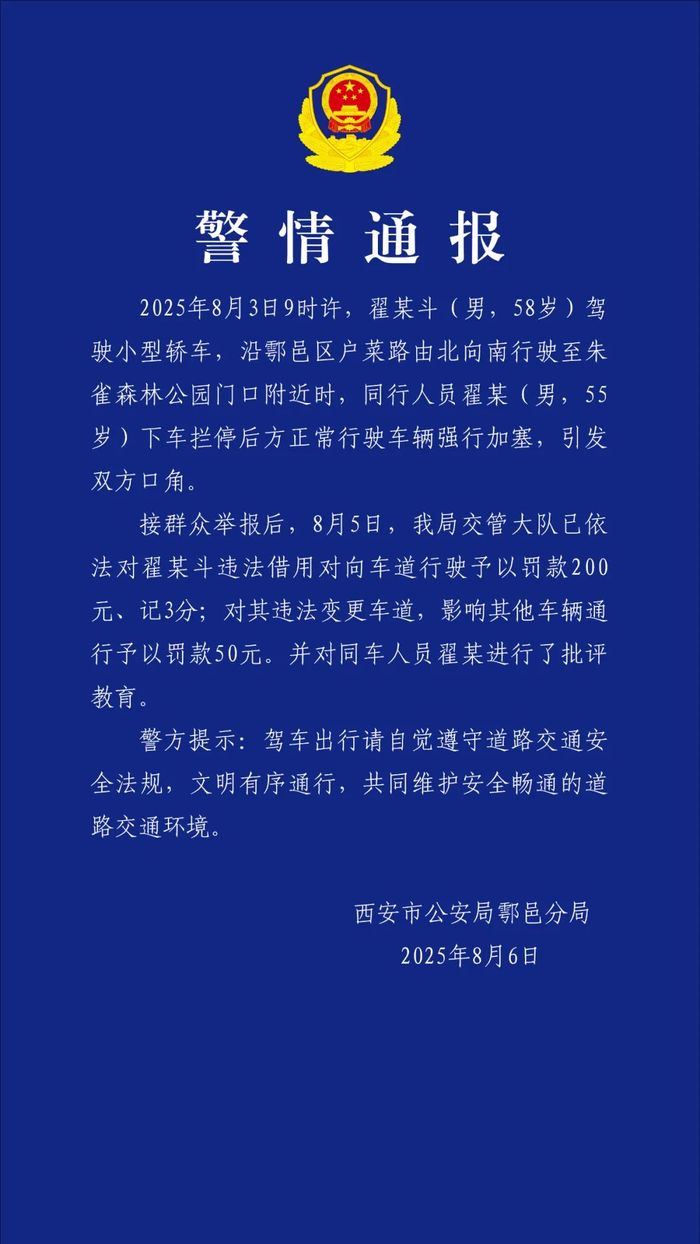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