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图源:视觉中国
作者 | 杨海滨
编辑 | 柳逸
(澎湃新闻·镜相工作室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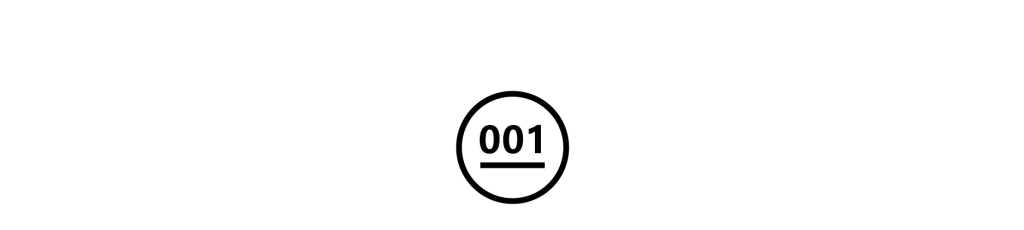
高原上的拳脚与“规矩”
“形势危在旦夕,”李小猫说,“二十多个当地司机,和他们叫来的三十多个帮忙打架的人,站在离我们三十米外的大巴车前,用青海话谩骂我们三十个从洛阳来的司机。我们也不甘示弱,操着撬棍、铁锹伏在掩体后观察着,随时准备迎击。”而黄队长却说,“我们是外来者,能忍则忍,不要轻易先动手。”这话让大伙一直保持静默,这场一触即发的斗殴在对峙了好一会儿后又转入僵持。
这事发生在2003年3月20日下午青海钾肥厂工区——这里地处大柴旦西一百五十公里外的大戈壁上——由于海拔高天空低,地平线显得辽远,即使双方加起来近百人,亦显得像蚂蚁般的稀疏和渺小。
“他们派人去大柴旦找人和咱们打架。”六小时前,李小猫在戈壁滩的宿舍里听黄队长这么说时,觉得有些愧疚,由于自己一时之怒,和当地司机打架,连累了大家,毕竟大伙是来挣钱的,不是来打架的。李小猫想化解危机,悄悄溜出宿舍,在戈壁滩上来回走了十分钟才找到信号,忙站定用电话报了警,但不确定警方是否能来,毕竟这里百里无人烟,出趟警像跑趟长途。他怏怏不乐地回到宿舍,焦灼地等待最担心的时刻到来。

车队住处(李小猫供图)
这场斗殴的起因很简单。今天凌晨三点,李小猫开着卡车跟在青海车队一辆卡车的后头,爬到数米高的料场顶卸货,那个一看就是新手的司机,在很窄的料场顶来回转了半小时,也没找到卸料地点,他在不耐烦中瞅见有个空位,便快速挂挡将车屁股插进,哗啦一下卸了货。不过,按规定,料车卸货要排队。
可这动作却惹怒了那位司机,他把开着大灯的卡车横在李小猫的车前,灯光照亮了这片空地。“为什么插队?懂规矩吗?”“你卸不了料我也不能卸?”他的反问激怒了那司机,司机踩着轮胎爬到驾驶室前,拉开车门揪着他的衣领“你给我下来!”李小猫毫无防备地随那人跳下车,压抑的火气一下被点燃,“信球货!”,他一把将那人推开。“你敢骂老子!”那人抬手朝他的头部打去,被他一转身闪过。
以前李小猫在河南老家的村小学当老师时,跟着体育老师练过几年太极拳,有点功夫底子,这时他一发力便把那人打倒在地。可没料到那人从地上爬起后,从驾驶座后拿出一把藏刀朝他刺来,他再次闪过,还一脚踢飞藏刀,挥起一直握在手中的手电筒,雨点般朝那人打去,直到对方求饶才住手。他想着事情结束了,便上了卡车继续装车运料。
黄队长在清晨听说了这事,很气愤,他开车到数十公里外的厂部,找领导反映情况。领导沉思了半天,“你们两个车队的俩领导平时就不对眼,你们的进入动了他们的蛋糕,明白吗?我看这事得你们自己解决。”
大伙听说了这情况,都觉得已无退路。“鸭子毛!”这是黄队长的口头禅,“既然出了事就不怕事,路喜庆,你领着修理组准备家伙自卫,同时用挖机在宿舍前挖条沟,防止他们直接冲过来。李小猫,你带着大家在宿舍前垒一道掩体做准备。”
这天发生的事,在李小猫的日记里被细细记录。
大家准备好后,路喜庆站在一辆大卡车驾驶室的顶部,朝远方瞭望,其余人不是抽着烟,就是雄心勃勃地讨论着咋打架。李小猫忧心忡忡。
下午四点,在卡车顶瞭望的路喜庆大喊:“来了来了!”黄队长问:“鸭子毛!看清啥车了吗?”“大巴!”“几辆?”“一辆!”路喜庆有点结巴地说。黄队长面对大家,“说要来三大巴车人,可见净吹牛逼。只要我们敢玩命,他们就怕!”这话鼓动着大家准备最后一搏。那辆像甲壳虫的大巴,在冒起的尘烟中,渐渐变大变清晰,然后停在距离掩体三十米外的地方。
从车上跳下三十来号人,其中几人上到车顶朝这边张望,讨论着什么。
青海那帮人没贸然行动,在对峙一个小时后,仍按兵不动,不过嚣张气焰已减一半,甚至有人回到了大巴上。就在形势趋于平息时,路喜庆突然跳出掩体,歇斯底里大喊,“老子跟你拼了!”形势忽然再起波澜。事后他解释说,当时神经绷得太紧,出现幻觉,以为他们打过来了。这举动被一边的李小猫按住,可对手已看到他的冲锋,条件反射地朝他们冲来,恰好在这时,远处一辆警车冒着尘烟,鸣笛驶来……
这是李小猫在青海的生存状况中的一个切片。“跑长途货运的司机,是没有生活的,只有如何生存。”多年后李小猫对我回忆道。

高原上行驶的货车(图源:视觉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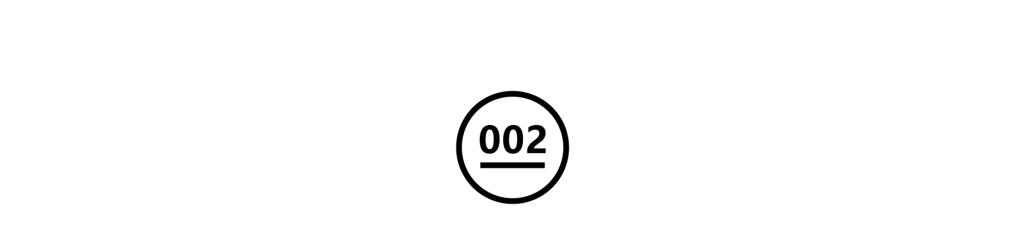
仙境的启示
2003年初,李小猫接受了朋友老黄的邀约,辞去了当了三年的小学老师的工作,在信用社贷了几万买了辆德龙F3000货车,跟他去青海跑运输。原因是他家所在的村里教育质量太差,两个儿子考大学不容易。为了让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李小猫把家搬到洛阳市郊,托关系进了市里的学校。但市里学费生活费不便宜,给家里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恰好这时老黄说他要组个车队去青海跑运输, 他说“青海地广人稀,只要有车,钱就好挣”。老黄的这句话,让李小猫生活的轨迹从洛阳走向了青海高原。
离开洛阳的第三天,李小猫开着车从海拔二千米的西宁行驶到日月山下,他沿着蛇身一样蜿蜒的盘旋山路开,到达二千米以上的山顶时,已是晚上十点。不料半夜时,轮胎在平坦的柏油路上爆了,他不得不跪在地上,卸轮胎螺丝。天很黑,于是他只能用手电筒照着。地上的砂石像钉子似的,硌得他膝盖生疼。刚卸下三个螺丝,他就坐在冰凉的地上喘起粗气,那种重感冒般的头疼,让他知道高原的严酷。
他咬着牙,付出了比平日多数倍的力气,才卸完螺丝补了胎。可没走几公里,他又发现后门上的旋转套坏了。开挖机的路喜庆帮他把旋转套割掉重换,这才修好。新卡车在内地是十八岁的青年,可一到高原就变成七十岁的老翁,李小猫明白了,接下来的生存将伴随着疼痛。
昨晚在甘肃某服务区夜宿时,保安不时敲门,提醒他小心燃油被偷,所以昨晚的李小猫每二十分钟就要从卧铺爬起,用手电筒照射倒车镜,观察右侧的油箱。昨晚的缺觉导致他现在极困乏,而眼下G109国道很窄,想找个能会车的地段都没有。他困得两次差点把车开到路边,忽见有处堆放石料的空地,他赶紧停车跳上卧铺,倒头就睡。
“因为天很黑,我也不知道把车停在了哪里。”第二天早上,李小猫被冻醒,透过车窗一看,水光潋滟的青海湖出现了,从湖边的淡青过渡到墨色的湖心,沿湖的山峦像画,天空蔚蓝,美得惊心动魄。一头头牦牛在静谧中站立,被牧女挤着奶,这境界简直就像他少时的梦境,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置身于仙境。
李小猫贪婪地咀嚼着这梦境般的景致,直到太阳把青海湖煮得沸腾,他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从平原走向高原,是为了摆脱那些焦头烂额的琐事,可这一路上,他反而遇到了更多的琐事,一地鸡毛。他还预感到,今后的琐事会更多,但眼下的仙境,让他一下明白命运的暗示:即使生活中有太多的艰难,也会有柳暗花明的境界,但需要努力走进去。他说,他那次主动迎接困难的高原远行,就是这仙境给予他的启示。

戈壁上的马海工区(李小猫供图)
这天傍晚他到达戈壁上的青海钾肥厂马海工区。车队有二十多辆卡车,运料更是二十四小时轮着转,每天需数吨汽油。最近的加油站在一百五十公里外的大柴旦,中途油量告急十分麻烦,这就需要一个油罐储油。但这时正是青海最冷的季节,油罐放在地上会冻裂。李小猫想起老家的红薯窑,即使冬天也不会把红薯冻烂。于是他自作主张让路喜庆开着挖掘机挖起了坑,也没给黄队长打招呼。
“埋在地下万一漏油咋办?”黄队长果然不同意。“不埋起来还不冻成冰疙瘩了?”黄队长不再吭声——其实他也不了解高原。次日一早,李小猫打开油罐盖加油时,发现油罐空了。黄队长说:“这不是漏油是什么!”路喜庆开着挖掘机挖开后,大家一看,果然油罐一角有个黑色的小洞,四周的砂石全被浸成汽油色。换一个油罐已来不及,也没条件,黄队长让他和路喜庆开车去格尔木找电焊师傅来马海工地,花了三天才把油罐补好。
“这是工作中的意外,更意外的还是那天我在料堆顶和当地司机的冲突,差点引发群殴。不过有时必须迎面而上,才能赢得生存的主动权。”

义气与生存,泥沼与鲜血
那天下午结束对峙后,黄队长通过朋友接到了西藏那曲一段公路砂石运输工程的活儿,所以他们第二天一早就离开马海,中午就上了可可西里公路。
行至中途,打头阵的李小猫看路边有一座立着“昆仑神泉”石碑的凉亭,便停下车招呼大家下车休息。他早听说这是传说中王母娘娘的家用水井,能治百病,现在看着沸腾的泉水,他一时忘了前路渺茫,信口拈来一句诗:“昆仑山中一眼泉,碧波荡漾欲漫沿,手掬一棒甘如蜜,众客疑为天上来。”黄队长撇撇嘴:“你再有文化,还不是跟我这没文化的人一起开车挣钱。”李小猫一下沮丧得无话可说,上了车继续前进。

青海高原大雾中行驶的货车(图源:视觉中国)
过了索南达杰纪念碑十公里,李小猫看见路边站着个人向他招手。坐在副驾驶位的路喜庆说:“这荒天野地的,谁知道是啥人,不能停车。”李小猫觉得有道理,可当车驶到那个年轻人面前时,他见他孤苦地在招手,心想都是出来打拼的人,能帮就帮一下,于是停了车倒回那人跟前。
那人原来是中铁十局的,他驾驶的越野车在勘探途中被困在了离国道三十公里外的沼泽中,人是步行到国道边的。“师傅帮我一下吧,把车拉出沙坑,我两天没吃东西了。”他的语调中带着哭腔。李小猫一下心就软了,随手拿着在马海带来的一个饼子跳下车,递给那个年轻司机,“别急,慢慢说。”
黄队长坐的车从后面上来了,一听说是中铁十局的车被困,甚至有点兴奋,“我们去西藏修的公路,就是中铁十局发的包,这忙得帮。”他便让李小猫和皮卡车司机换了车,又让维修技术好的路喜庆也上了皮卡,再与车队约定,晚上在前面五道梁会合。戈壁荒芜,路途颠簸,路喜庆被颠得反胃:“那些身体好的你不挑,非让我来。”抱怨的话音未落,他又吐出一股浊流。
可可西里在酷寒的冬天,能把沼泽冻成坚硬的地面。可到了风沙大的春季,沙子把表面的草苔覆盖,让人看不出下面是沼泽还是戈壁,这时汽车轧上去就会被沼泽吞噬。他的车就是两天前误行到这上面的,瞬间顺着流沙滑进了山头下的沼泽,“我没经验,还想把车开出来,哪知一踩油门,车的大半身陷得更深,如果不逃出驾驶室,我有可能会困死在车里。”年轻的司机说。他费尽全力爬出后,才跌跌撞撞走到国道边堵车求救援。
他们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才到那里,看到那辆越野吉普陷在一处谷底沼泽中,露出半个车身。他们四人把钢丝绳挂到皮卡和越野车上,可在拉车时,中铁十局的年轻司机却说:“我腿软得厉害,不能开车,请师傅们帮个忙。”黄队长一愣,然后看向路喜庆。路喜庆连连摆手:“饶过我吧,当地的司机都不敢上,我这山里人哪见过这场面。”“鸭子毛!”黄队长骂完便转过头对李小猫说:“我上越野,你鸣笛为号,一鼓作气拖上来。”
黄队长斜着身体下到沙坑,扒开车门前的稀泥钻了进去,车身也随着他的重量又陷进一截。李小猫屏住呼吸缓缓加油,钢丝绳慢慢绷直后按了下喇叭,皮卡的轮胎刨着地面,在颤抖中发着匀力,越野车一点点脱离沼泽坑。就在李小猫以为成功时,突然钢丝绳断裂,传来“哎呀”一声惨叫。他寻声一看,钢丝绳的断头打到了站在一边观望的路喜庆的脸上。
他忙跳下车到路喜庆跟前查看他的情况。路喜庆脸上开了道血口子,像嘴唇一样翻起,鲜血像湖水一样漫开。李小猫忙到皮卡上找急救用品,但车里除了一卷卫生纸什么都没有,他和黄队长只能慌忙把一卷纸都糊在路喜庆脸上,好歹止了血。
李小猫看着沮丧的黄队长说,“别担心,刚才我看到皮卡上还有根粗钢丝绳。”黄队长的脸转晴,俩人再次连好车,越野车如老叟上坡,颤颤巍巍被拉了上来。
李小猫把躺在地上疼得直叫唤的路喜庆扶上皮卡,驶向国道,等赶到五道梁与大队人马汇合时,已是凌晨五点。他知道路喜庆的伤口很严重,须马上处理,尤其在高原上,一旦感染得不到及时治疗,就会有生命危险。车队当即将五道梁找了个遍,才终于看到有红十字标识的两间平房。可穿白大褂的中年女子看了伤口说:“医生到格尔木去了,生理盐水和消炎药都用完,也没有条件做缝合手术。”
黄队长跟李小猫一商量,堵了辆便车,让路喜庆回西宁治疗。路喜庆还不乐意,嘟囔着“我还没挣一分钱”。可自此分别后,他再没见过路喜庆,听说他到西宁后因没钱没去医院,直接回洛阳了。
直到十年后,李小猫结束青海货运生涯回到新安老家,才听说路喜庆当年因感染治疗不及时,早已不在人世了……

货车抛锚(李小猫供图)

“精神的爱人”,在布哈河岸
一年后洛阳车队随着黄队长回河南而解散,司机们各寻各路各挣各钱。李小猫一年前在依吞不拉克拉铁矿时认识的老田夫妇,听说此事后,给他打了电话,“我正准备去德令哈拉矿石,不如你跟我一起去!”就这样,他随老田夫妇来到德令哈。后来,李小猫又从德令哈转到天峻县,准备跑木里至西宁的煤炭运输。

李小猫在德令哈时的住所(李小猫供图)
布哈河发源于疏勒南山的岗格尔雪合力冰峰,一路穿越天峻县全境。从木里煤矿拉煤,须沿河岸经阳康乡的“天木公路”到达天峻县城,而乡政府就设在公路边,这里有五家清真拉面,两家川菜小店,是路过的司机们休息、吃饭的地方。
李小猫每次路过阳康乡,都会直接去西头那家叫“马小梅清真拉面”的拉面馆吃饭休息,碰到客人多时,他还帮端饭倒茶、招呼客人,同时和老板娘谈笑风生,宛如一家人。他也总是最后一个吃完饭的,在女老板的陪伴下给卡车加水、洗车。“我和这个女人有些说不清的暧昧,她在我那几年孤独的生活里,像一股温柔的风,慰藉着我。”李小猫回忆。
一年前,李小猫刚开始跑煤炭运输,第一次出车的那天早上7点,他刚把车开到公路上,就看见有个围着方格头巾的三十来岁的女子在招手搭车。他本想无视,可想着刚来天峻,和当地人聊聊这里的情况对自己熟悉环境有好处,何况眼前的又是女人,就停了车。“师傅,把我拉到阳康吧。”他没想到,女人还有一框西红柿、一框西葫芦、两袋五十斤的面粉。“麻烦师傅帮我扔到车厢里。”她的口气像是他是她多年的相识,李小猫不自觉地接受指令,跳下车,嘟囔着,“坐我车还要我帮忙。你拿这些东西干啥?”他好奇地问。
女人坐进驾驶室,松了口气,“我在阳康开了个拉面馆,以后你经过阳康到我那吃饭。”“这种体力活让你男人干,你一个女人不辛苦?”“我一人干饭店。我没有男人。”他一时语塞,辽阔草原的景色在车窗外飘渺着,女人看出了尴尬,“我男人家暴,实在受不了了,跟着一个姐妹从白银逃到天峻,在县城一家清真饭店帮了一年厨,现在在阳康单干。”他听了就不再接话。
到了阳康,他帮她把东西卸下车,女人想请他到另一家拉面馆吃饭,他因急着赶路,就拒绝了。但俩人却留下了电话号码。这女人就是马小梅。此后,她成为李小猫在青海的孤独生活中的“心灵之水”和“精神爱人”。
后来,李小猫每次经过阳康都会在马小梅的拉面馆吃饭,“在哪个拉面馆都是吃,在她这一则能照顾她的生意,二则聊得也投机,精神上舒坦。”
再后来,马小梅在阳康数次给他打电话,要他从天峻县帮她带面粉,还有几次带蔬菜,她人都不用出面,而且每次他从木里拉煤到阳康,都会特意把大块的煤装在麻袋里,卸给她用,解决她饭店的燃料之难。为感谢他,马小梅在这年夏天专门从牧人那买了只羊,提前打电话要他在阳康休息一天,恰好那天县上的小姐妹也来看她,三人一起来到布哈河边的草滩上,撑起一顶白帐篷,把羊杀了,煮羊肉手抓灌血肠。马小梅的小姐妹还开玩笑地喊他“姐夫”。
某天,他在她的饭店吃拉面时,她瞪着眼看着他,他心里一颤。“我俩一起去阿里吧,到那开个拉面馆,一定比在阳康挣钱。谁也找不到我们,我再给你生个孩子过日子。”他一阵惊吓,觉得女人的眼光变成布哈河的洪水,淹没了通往河南的道路。他想起在老家操持着家务的老婆忙碌的身影,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这一切辛苦,都是为了这个“家”。
正不知如何回答时,手机突然响了,田嫂在电话里高声说:“我的车坏在快尔玛了,你在哪呢?快来帮忙修理。”他如释重负,轻叹了口气,“我得赶紧去帮老乡修车。”然后把碗筷一推,第一次没像往常那样帮忙收拾餐具,起身走到车前,再爬上车,把备好的一麻袋大煤卸下,背到她的饭店内。
“我的话你要认真考虑。”马小梅站在门前看着他说。他一脸严肃地点着头,和以往在分别时一样,说了句“再见”,这话出口时,他觉得有一语双关的意思,“以后不会再见了”,他边走边想,背上立刻有了刀戳般的疼痛感。但他知道,即使自己目前正处于感情的荒漠,有些事也不能越线。他决定让心归于家庭。
回到西宁当天,他接到以前车队同乡的电话,邀他到肃北拉铅锌矿石,说那里非常需要货车,而且收入也好。卸完货,他直接朝肃北驶去,把布哈河河岸上的暧昧感情抛到了脑后。
一年后,李小猫收到马小梅从阿里打来的电话,“我一人在阿里开饭店,就差你来给我拉煤了!”听到这声音时,他心里又潮湿了起来,长时间说不出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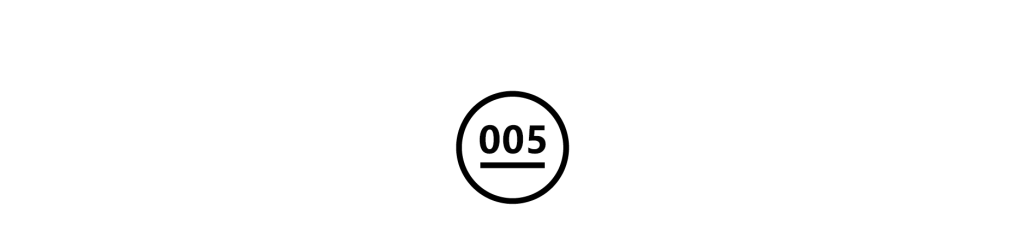
关口与枪口
那年冬天,一个下午,他拉货去花土沟,戈壁滩上的公路数百公里都是笔直笔直的,伸进无尽的前方,路两边是辽阔的荒凉,像复制黏贴的一样,也没个参照物,极易让司机麻痹。“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走到天黑,才意识到错过了G315与大柴旦的交叉口,车子已经往鱼卡方向开了几百公里。”
如继续往前,到达涩北工业区绕个圈去花土沟的话,中间要经鱼卡检查站,还要交200块钱的过路费,但这又是最近的走法。如按原路返回,到G315国道与大柴旦分岔口,再去花土沟,则要多走一百多公里,很不划算,两者相比,前者最节省时间。
在海西跑运输,全州公路上有几个检查站,用什么方式检查,他都了如指掌,也知道鱼卡站的检查人员配有枪,是最严的一站,李小猫在黑暗中听着发动机的轰鸣,盘算着到底该走哪条路。但想到那200块钱的过路费时又犹豫了。“对像我这样一路吃十块钱一碗面的司机来说,这笔过路费不亚于割肉。再说,是我分心走错了路,本不该出这钱。”现在是夜晚,来往的卡车也不多,鱼卡检查站的人不可能24小时高度警惕,总有疏忽的时候,如能找个机会闯卡,既能省下那笔钱,也能免去多跑一百公里的冤枉路。这样怀揣着侥幸想的时候,他便决定了——夜闯鱼卡检查站。
接近十二点时,他开着车到了鱼卡站前的公路处,为避免发动机的声音惊动检查站的人,他熄了火,也关掉了大灯,在暗中观察着检查站的情况。“整得像特务夜过国境线似的”,想到这他兀自笑了。
戈壁滩上刮着的风这时更大了,砂石像盛开的小鞭炮,敲打着他的车门,总觉得有点心惊肉跳,但他还是连续观察到了凌晨两点,发现检查站玻璃岗亭里一直空无一人,只有一盏灯暧昧地照亮寂静的黑暗。“这时是人在生理上最困乏的时候”,他在心里一边默默祷告着,“警察叔叔,风太大,不麻烦您出来检查了!”一边猛踩油门,卡车像百米冲刺的运动员朝前冲去。
就在他以为成功时,旁边的排房里突然闪出一个警察,示意他停车,并用手枪对着他。刚才因紧张而沸腾的身体,瞬间被冒着冷气的枪口冷却,准备了半夜的勇气立刻泄了气。
“(闯关)这就像我的生活。”李小猫说。
他还会继续在戈壁上行驶,有时抱着勇气,有时抱着罪恶、侥幸和狡黠。
(文中人物除李小猫外,皆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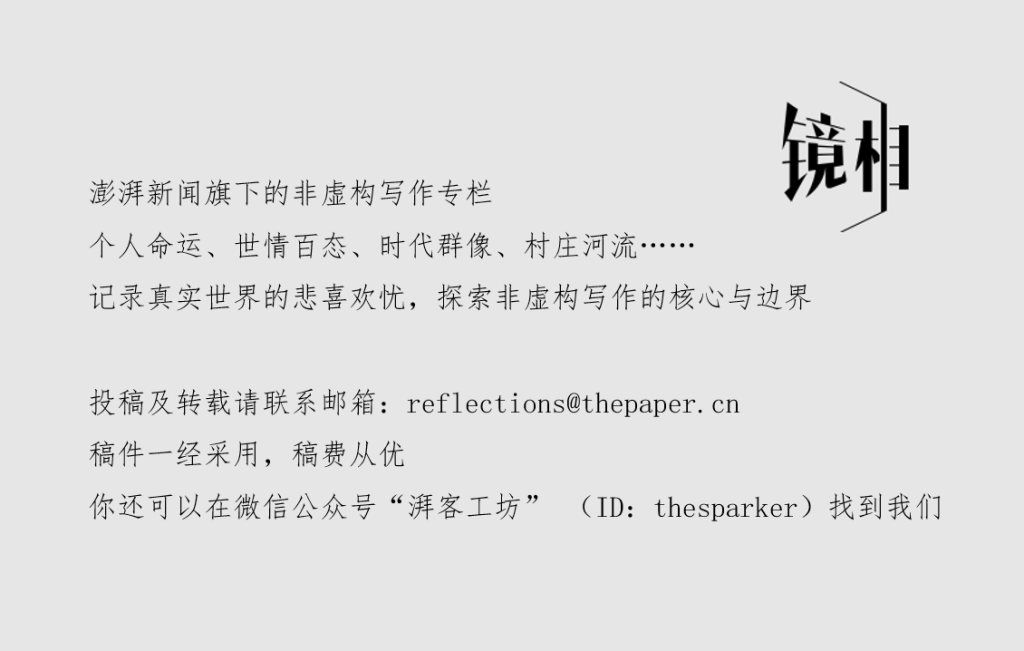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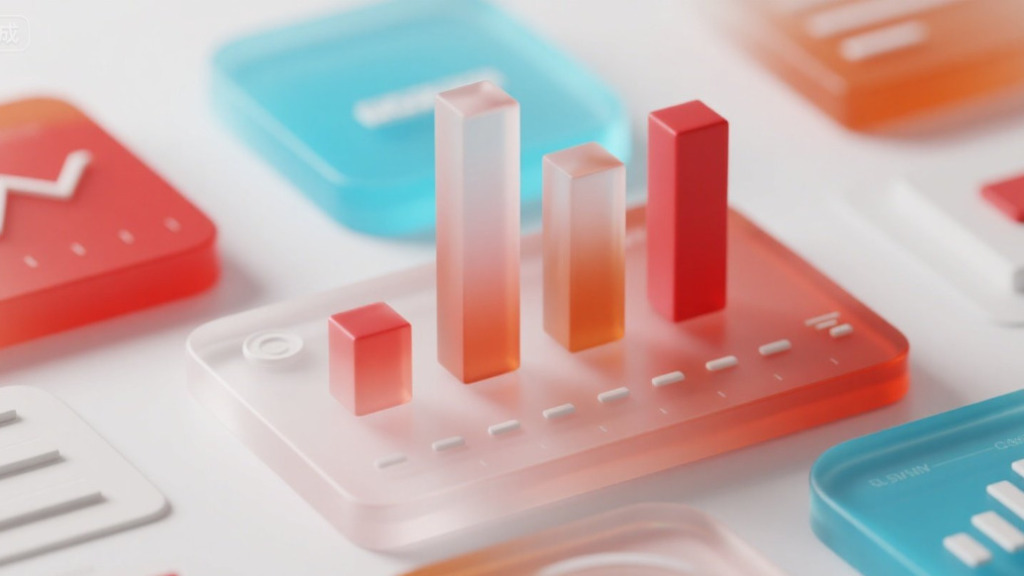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