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涂瀛论《红楼梦》,有几处意料之外。一是林黛玉应有家资,并不如历来以为,孑然一身入贾府,扬州奔父丧回来,不过带些书籍。宝玉曾向王夫人提供一副丸药方子,耗资三百两银子,保管妹妹药到病除,在座人不当真,只作玩笑,凤姐倒作证确有此方,但又把话题扯到薛蟠身上,引得王夫人念咒:“阿弥陀佛,不当家花花的!”宝钗建议每日吃燕窝粥,滋阴补气,她顾虑道:“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纸,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那起小人岂有不多嫌的。”最后宝钗承担下来,暗地遣送燕窝冰糖,添补了这项额外的用度。黛玉病情沉重,紫鹃托周瑞家的问凤姐预支月钱,凤姐秉公办事:“一个人开了例,要是都支起来,那如何使得呢。”送了几两体己了事。倘要是有自家的钱财,何至于要吃这个软钉子!按常理推,林如海称得上世家,祖上袭过列侯,起初封袭三世,承隆恩额外加封,又袭一代,到他辈,便从科第出身,殿试取第三名,探花,升至兰台寺大夫,其时钦点巡盐御史,鹾政扬州。(按,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一九八一年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的三卷本《红楼梦》,“兰台寺大夫”注为:“兰台是汉朝宫内藏书的地方,由御史中丞主管,兼任纠察。后因称主管弹劾的御史台为兰台,御史府也叫兰台寺。”)官品相当高了,而“巡盐御史”则是有实权的。众所周知,清初扬州位于运河沿线,是为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食盐供给基地,两淮盐业的八大商总聚集在此。曹雪芹祖父曹寅曾任两淮盐漕监察御史,去世后,由其内侄李煦继任,多少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头,单是派发盐引,即经营牌照,控制产销和税收,明里暗里通融,就生出多少利好。就算林如海出身书香之族,洁身自好,按清代养廉银制度,正当收入也是可观。所以,林黛玉当有遗产继承,那么钱去哪里了呢?涂瀛给出一条线索,那就是林如海发丧,由贾琏陪同黛玉前往装殓,话说到此,便可收起,否则,就变成推理小说了。
想不到处第二,在“莺儿赞”一节,宝玉、宝钗成婚,照例袭人、莺儿同是收房大丫头,好比凤姐的平儿,薛蟠尚未正娶,先收了香菱,赵姨娘、周姨娘大约也是贾政的贴身丫头,或者王夫人的陪房。袭人早在提亲之前,就已经内定,所以很关心谁是大太太,为自身处境想,力挺宝钗,排拒黛玉,不负苦心得其所哉。再然后宝玉离家,袭人发放出去,当正配的迎娶,嫁于蒋玉菡,恰就是宝玉的旧人,终修得正果。莺儿呢?“赞”中写道“郑灵之鼎已无异味矣”。典出《左传·宣公四年》“楚人献鼋于郑灵公”的故事,郑灵公熬制羹汤,请众大夫共享,偏不分公子宋(字子公),子公自行伸指沾鼎中羹汤,拂袖而去,即日后“染指”一词的来历。宝玉素常和莺儿亲密,袭人请莺儿到怡红院打络子,莺儿发表一番颜色的弘论,把宝玉镇住,见她“娇憨婉转,语笑如痴”而“不胜其情”,说道:“明儿不知那一个有福的消受你们主子奴才两个呢!”不料想,自己倒成了“有福的”。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不止莺儿,连秋纹、麝月一干人都不见其踪。要知道,这两个可是过了王夫人眼的。抄检大观园之后,王夫人亲到怡红院视看,撵走大半女孩子,宝玉哭向袭人:“怎么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单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纹来?”却没有逃过又一轮清理阶级队伍,试期渐近,宝钗和袭人两个商量,生怕宝玉再犯轻薄的老毛病,将身边人一一点数,“狐媚子”五儿要嫁人了,麝月、秋纹是和二爷顽皮惯了的,好比有了前科,就靠不住了,唯有莺儿稳重,而且宝玉不大理会。这就和前番形象不符了,或许受宝钗调教,抑或有晴雯的前车之鉴,改了性,留她带着小丫头服侍,仅够用的了。及此,卧榻之侧,再没有异己。
这两宗隐情,显然出自世事洞察所见,不属“红迷”通有的缠绵悱恻。而公认成显学的疑案,可卿之死,却未曾提及。“论赞”中一节形容她的柔媚多情寿夭,遭际则非属天灾,而是人祸,似有暗示,但浅尝辄止。参看“贾珍赞”,满纸痛骂,也未有涉及。读花人既是市井见识,又似有洁癖,凡阴晦龌龊都避之不及,“问答篇”专列一项,为妙玉翻案,就是从此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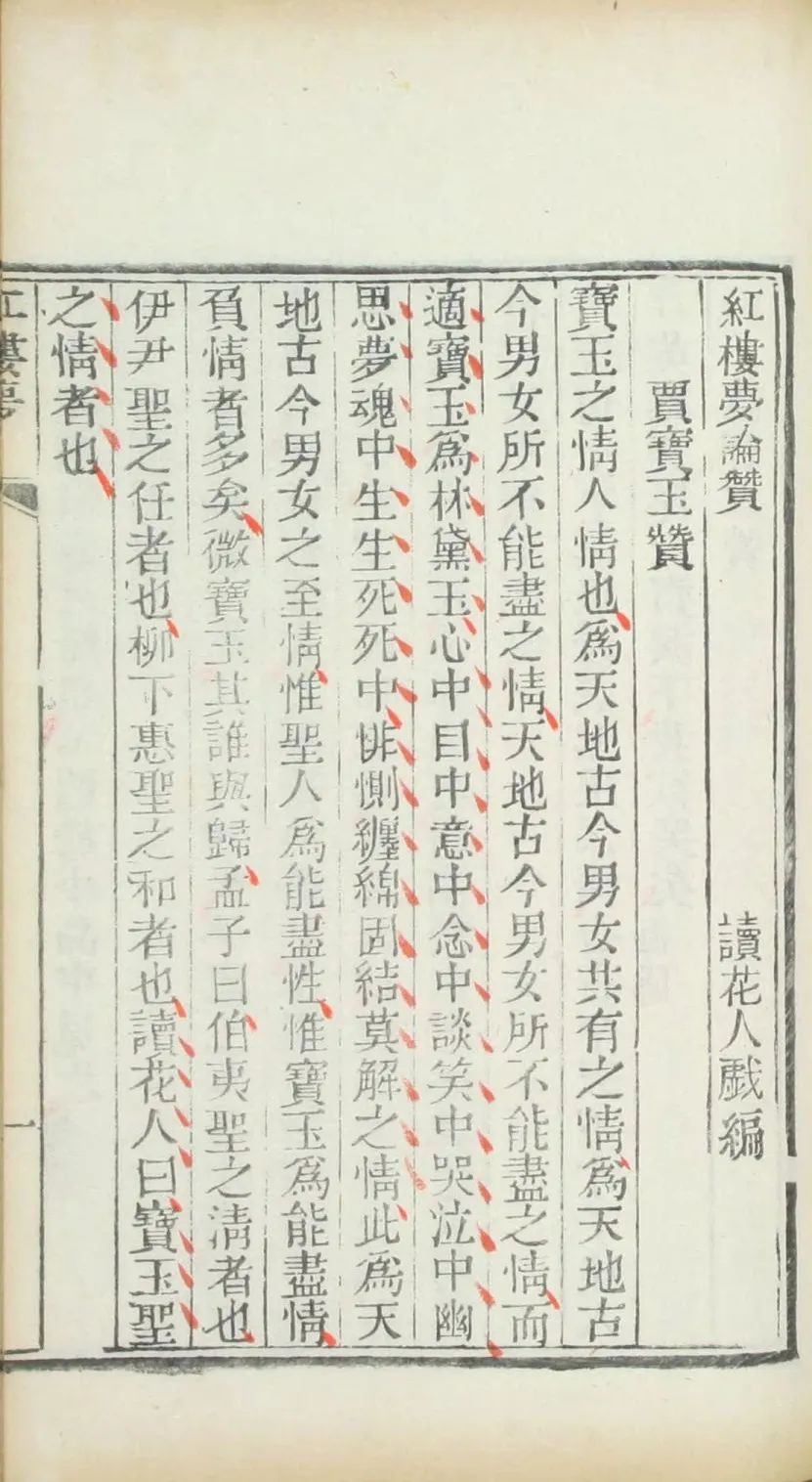
读花人《红楼梦论赞》(收入《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
涂瀛,字铁纶,号读花人,清道光年间人,生平记载多以“红学家”称,存世《红楼梦论赞》《红楼梦问答》,收录于王希廉《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我对古典文学有隔膜,所知甚少,不善查考,只能从文本中求实。何炳麟跋文称“桂林铁纶涂君瀛”,又一跋者邱登写“昔宦桂林牵率尘网风雨扃户有石其语”,邱登亦写“红楼梦赞”,文字中有“桂林涂铁纶孝廉瀛深情人也”。籍贯桂林不会错了,中过试场,做过官,又卸官,钟情于“红楼”,自号“读花人”,必是才子气重。桂林这地方,历来有“山水甲天下”之誉,明清为广西省会,辖区内地名:秀峰,叠彩,七星,雁山,象山,仿佛大荒山无稽崖青梗峰。涂瀛文章以尘世论“红楼”,“贾雨村”说“甄士隐”,用邱登话“翻空妙惟征实”,颇有些类似张爱玲说杨贵妃和梅妃争宠,“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人生乐趣也就在此。太虚幻境美虽美,毕竟太过渺茫,不如常伦常态有共情。倘若牵强附会,国民政府桂系军阀白崇禧的后人白先勇,所写小说亦仙亦俗,人都是现世相,却有巫觋气,比如玉卿嫂。不定是通窍山水,又善解人意,方才将正史写成渔樵闲话。为揣摩读花人心思,却扯得远了。《红楼梦》一经问世,不知涌出多少读书人和评书人,也是时代风尚。自公元九世纪起始,长江中下游,便有书坊,司售刻本,到明清成鼎盛之势,那涂瀛先生不过沧海一粟。有次和宗璞先生聊天,说起高鹗的后四十回,请教先生意见,回答是肯定的,基本续得上曹雪芹前八十回,因为时代最接近。曹本八十回最早的抄本庚辰本问世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收入后四十回的程高活字本发行在乾隆五十六、五十七年,相距三十余年。《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刊行于道光十二年(1832),隔了嘉庆朝的二十五年,从全本到读评,满打满算又是四十年,许多人和事尚可前后兼顾。同一个王朝天下,所赞所问,应是切得着脉象,也就敢实写红楼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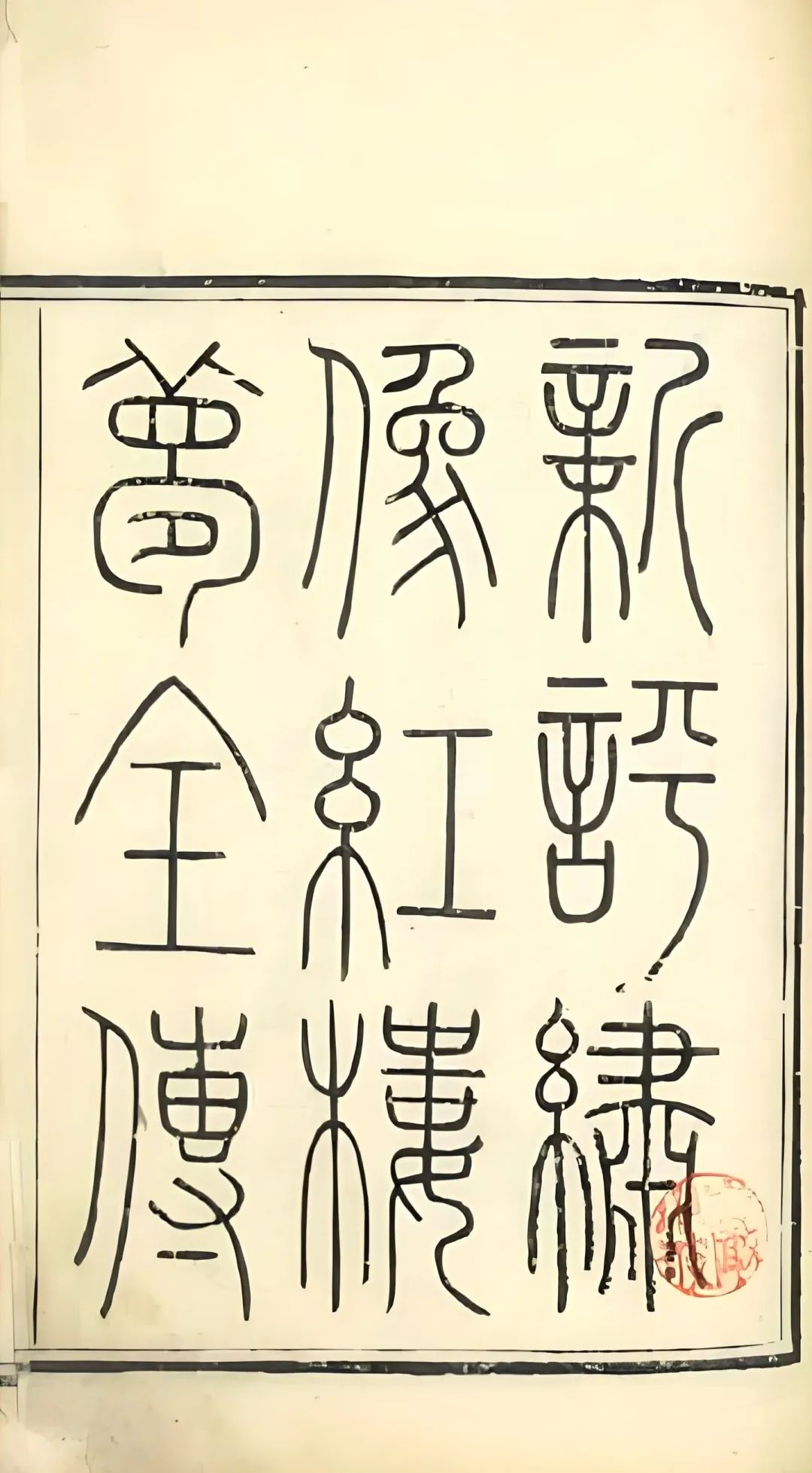
《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
“问答”第一题,“红楼梦伊谁之作”,大剌剌道“我之作”,理由“语语自我心中爬剔而出”,意思他说即我思我想。第二题则直指违和之处,那就是,既然如此,替妙玉翻案又是出于什么用心?小说第五回,宝玉入太虚幻境“薄命司”看册子,正册中的一页,画着泥垢中的美玉,断语:“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应得上第一百一十二回“活冤孽妙尼遭大劫”,公认册子的图谶指妙玉没有错。涂瀛偏别开生面,网罗另一路原委。“妙玉赞”一节来回读过数遍,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请年轻的同事陶磊帮忙。陶磊他古文有童子功,博士师从香港中文大学资深教授王宏志,研究佛经翻译历史,颇费一番脑筋,既要训诂,又须解评书人款曲,再加后现代解构主义,终释出原意。妙玉失踪发生在贾家式微,可谓外辱内乱,早已不是出家人修行之地。其时,贾母出殡,合家伴灵,只贾云、林子孝留守,恰逢强盗来袭,便趁乱放人。列举两条证明,一是“其师神于数者”,指的第十七回,林子孝家的叙述妙玉来历,说她的师父有遗言:“衣食起居不宜回乡,在此静居,后来自然有你的结果。”如师父先天神数,如何不提前报警,任由弟子遭此不堪?又有二,“而幻境重游,独不得见一面”,一百一十六回,宝玉失玉,闹得沸反盈天,不期然间,魂魄出窍,重游太虚幻境,先遇尤三姐,后遇鸳鸯,再是林黛玉、晴雯、凤姐、秦可卿、迎春,一干故人都任了新职,唯不见妙玉。按坊间传说,妙玉被抢了去,不能依从,被杀了,尘缘了结,而她尚未归籍。这极有可能误传,“然则其去也,非劫也”,实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问读花人竟然违曹雪芹初衷,另起首尾,其意何在?回答曰:“第觉良心上煞有过不去处!”犹可见出纯良性情,不忍使高洁女子落入泥淖。并非妇人之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俗套,而是善恶两分,不容半点混淆。第三问,能否自许宝玉,回答“能”,那么:“何以痛诋袭人也?”笑答“我止不能为袭人之宝玉”,意思大约是不能接受袭人。世人诟病袭人虚假不义,已成共识,读花人则更严苛,“论赞”中袭人一节,举北宋苏洵论王安石作比:“王安石奸,全在不近人情”,就比较容易提防;“袭人者奸之,近人情者也”,所以迷惑人。黛玉、晴雯死,芳官、蕙香被逐,秋纹、麝月受控,都与之脱不了干系。如若在宝玉离家走前死去,或可以贤名始终,偏偏老天留她在世,患得患失,终是苟且偷生,嫁给了蒋玉菡,一生真伪水落石出。这话说得狠,读来过瘾,批点人梅阁,亦跋者何炳麟称:“不作袭人赞读通,即作袭人赞读快”,即大快人心。甚而至于怨怼宝钗,这就需要一点胆识了,因是贾府上下无可指摘的得人心者,而微词正出自此,曰“深心人也”,再问“于何见之”,就在“交欢袭人”!读花人不免惘然,按“君子与君子为朋,小人与小人为朋”的普遍原则,宝钗和袭人分明两种人物,无论身份知识,都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吾不识宝钗何人也,吾不识宝钗何心也”!然后自问自答:“古来奸人干进,未有不纳交左右者。”用“奸人”比宝钗,情急之下,不免言重了。看“论赞”宝钗一节,措辞平和,却不减机锋。惯常例举的几项,不外偷听小红私语,甩锅给黛玉身上;金钏儿跳井,开解王夫人“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诸如此类,读花人不提,着眼人际关系:“以凤姐之黠,黛玉之慧,湘云之豪迈,袭人之柔奸,皆在所容,其所蓄未可量也。”所以谓之“心深”。然而,一旦利益交集,决不手软,比如爆料黛玉死讯,让宝玉断了想头,杀伐果决。“赞”中还列有一项“促雪雁之配”——从文中看,倒不是宝钗所为,只可说默许,又怎么能怪她?不是早有话在先:“女孩儿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亲没了,妈妈应该做主的,再不然问哥哥。怎么问起我来?”所以,本人无须担责半点。“赞”中还说,劝宝玉读书求仕,遭了冷脸,寻机反击。宝玉没话找话,说了句姐姐体丰怯热好比杨妃,不料宝钗大怒,回道:“我倒像杨妃,只是没有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杨国忠的!”紧接又借小丫头靛儿找扇子,厉声道:“你要仔细!我和你顽过,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跟前,你该问他们去。”这话就说得明白不过了,论赞者用了“泼醋”一词,指摘道:“所为大方家者竟何如也。”虽言犹过及,但揭开了温柔面纱下的真面目,露出峥嵘。
将“木石前盟”“金玉良缘”三生石上谶言束之高阁,不说仙缘,只说尘缘,合了人情洞察皆文章的古训,又是明清叙事文学的要旨。事实上,曹雪芹定然接触过话本传奇一类的通俗读物,“红楼”二十三回目“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就是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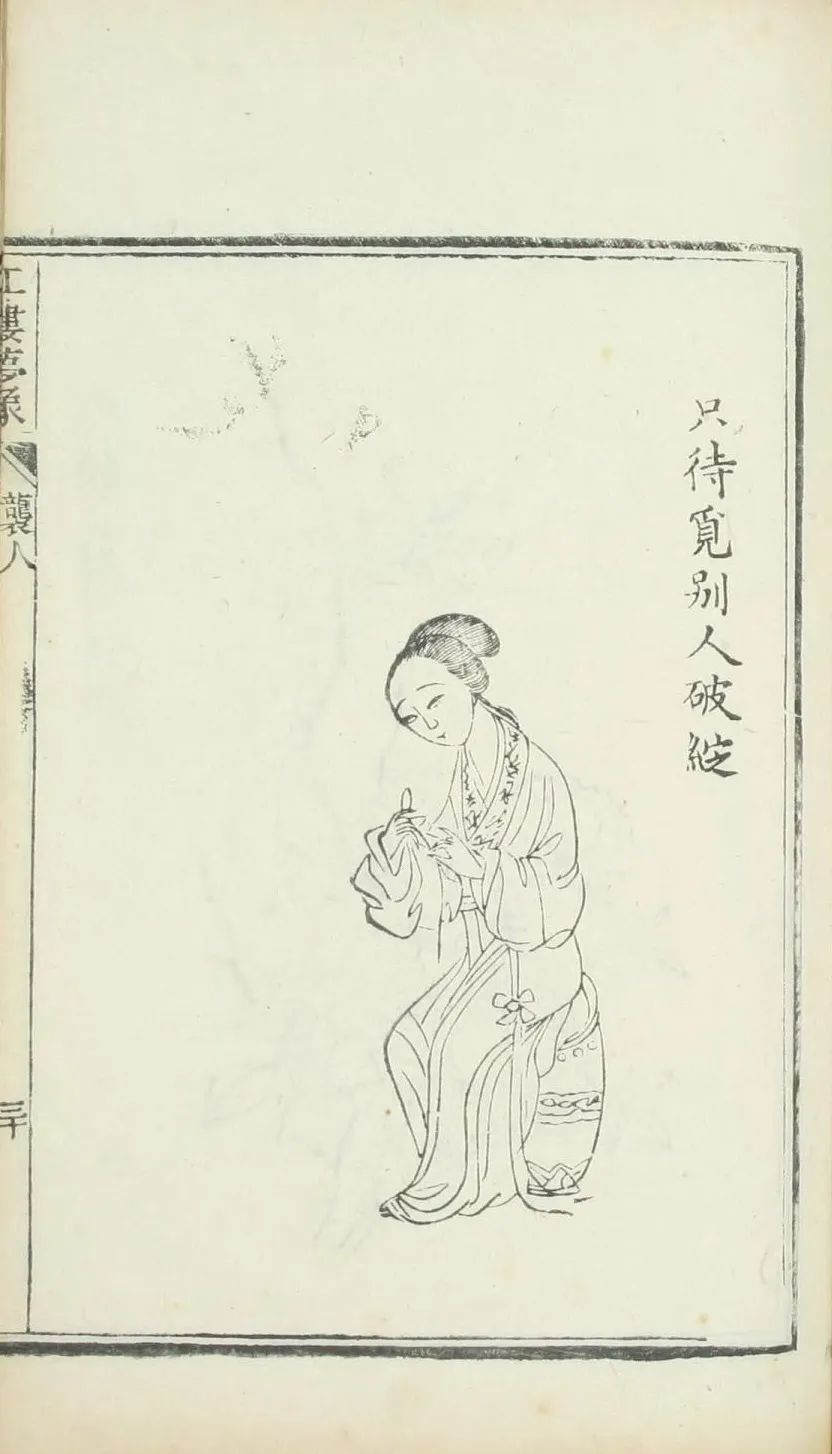
袭人画像(《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插图)
宝钗和袭人颇占了读花人的笔墨,除宝黛悲剧的当事人外,还因为这两位涉世心重。袭人尚可解释,身为奴婢,无有背景,凡事凭一己之力打下江山。宝钗呢,就费点思量了,大家闺秀,养尊处优,何须自谋前程,又哪里来的社会阅历经验,供她做谋划?身在阁中,可说处处掣肘,周转腾挪的余地更有限,如“问答”所说,“而故深之”,需旁敲侧击,才能显山露水。
《红楼梦问答》先以宝钗和黛玉作比:“宝钗善柔,黛玉善刚,宝钗用屈,黛玉用直,宝钗循情,黛玉任性,宝钗做面子,黛玉绝尘,宝钗收人心,黛玉信天命不知其他。”柔屈可应百变,刚直则易折;循情者因势利导,左右逢源;任性者一意孤行,进退失据;做面子者八面玲珑,绝尘者四方碰壁;收人心者耳聪目明,其实如履薄冰,贾母主持庆生,问有什么喜好,宝钗件件按老祖宗的口味,非平时留意,如何正中下怀?皇妃娘娘送出个灯谜,早已经有了答案,嘴上还一径说难。因为金锁和玉石相配的妄语,举止间时刻谨慎避嫌。信天命一说就需要些解释了,应不是“尽人事听天命”的宿业,或更接近庄子《逍遥游》中的自由世界。第二十二回,宝钗黛三人谈禅,宝玉为女孩儿们与他生隙,怄气写一偈:“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意即万境归空,才是立足之境。黛玉嘲笑他不彻底,续了两句:“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宝钗接着说一段六祖惠能的故事,以一偈“菩提本非树,明镜亦无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继承了衣钵,将形而上又降到形,无用无功回到有用有功。禅这样东西,实是佛的入世门,黛玉则是出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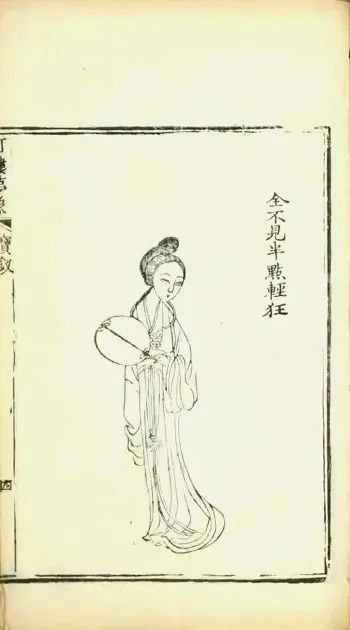
宝钗画像(《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插图)
读花人又将袭人与晴雯套用着来一问,袭人对宝钗,晴雯对黛玉。前者无须赘言,先头说的“交欢”一词便可证明,至于晴雯比黛玉,也有踪迹可循。贾府上层筹划端肃风化,收集下方意见,王善保家的特指出晴雯,王夫人向凤姐问,“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想必就是她了!晴雯死后,宝玉作祭文“芙蓉女儿诔”,黛玉闻知,与他商量其中“公子”和“女儿”的对句,先改成“小姐”对“丫头”,后定为“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黛玉顿时变色,仿佛听见谶语。所以,用涂瀛的话说,袭人是宝钗的影子,以袭人写宝钗;晴雯是黛玉的影子,以晴雯写黛玉。以“副册”“又副册”影射“正册”——太虚幻境的警幻仙姑所说,“金陵十二钗正册”即贵省中十二冠首女子,“副册”“又副册”则次之,其余无册可录的,皆庸常之辈。那座次,甚或无座次,其实是仙籍的人间相。而读花人自许宝玉,从他眼里看出去,位无尊卑,人无正副,唯有一别,有情和无情。
按影子说论,宝玉和黛玉的木石前盟有没有红尘投射?有,凤姐地藏庵拆散的姻缘,长安守备公子和张家金哥是“远影”,那都是上不了册子的庸常人物,好比云泥之别;贾蔷和龄官为“近影”——那龄官确有黛玉之风,元春省亲,钦点她再做两出戏码,《游园》和《惊梦》,她偏偏要本角戏《相约》和《相骂》,想是闺门旦的行当,前两折却是青衣戏。宝玉央她唱曲子,多少人巴不得的事,就是不从,心思全在贾蔷身上,蔷薇花下画“蔷”字,可谓黛玉葬花的别景。贾蔷其谁?宁府正派玄孙,父母早亡,说起来也是个纨绔,但在龄官身上动了真情。宝玉不由长叹,想即便一个园子里的,“我竟不能全得了。从此后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这是初悟。到第九十一回里,黛玉和宝钗前嫌尽释,与宝玉也无猜忌,风平浪静,却不知,大事已经裁定。宝玉疑惑宝姐姐对他冷淡,黛玉问道好和不好则又如何,愣怔片刻,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这一幕好像佛祖拈花微笑,终为彻悟吧。再接着木石前盟的人间投影——潘又安和司棋是“情影”,一同向生,一同向死;柳湘莲和尤三姐则是“无情影”,情生一地,天各一方。“无”不是相对“有”,亦不是“无”,而是“空”,即先前头里“好了歌”的“了”字。以那跛足道人的释解:“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柳湘莲装殓毕尤三姐,随道人堕入空门,实是宝黛结局的预演,因而称之“无情影”。远影、近影,有情、无情,都是现世相,射覆的宝玉、黛玉的真身,却是赤瑕宫神瑛侍者和三生石畔绛珠草。他们的盟约源出于“还泪”,有点类似西方人的“原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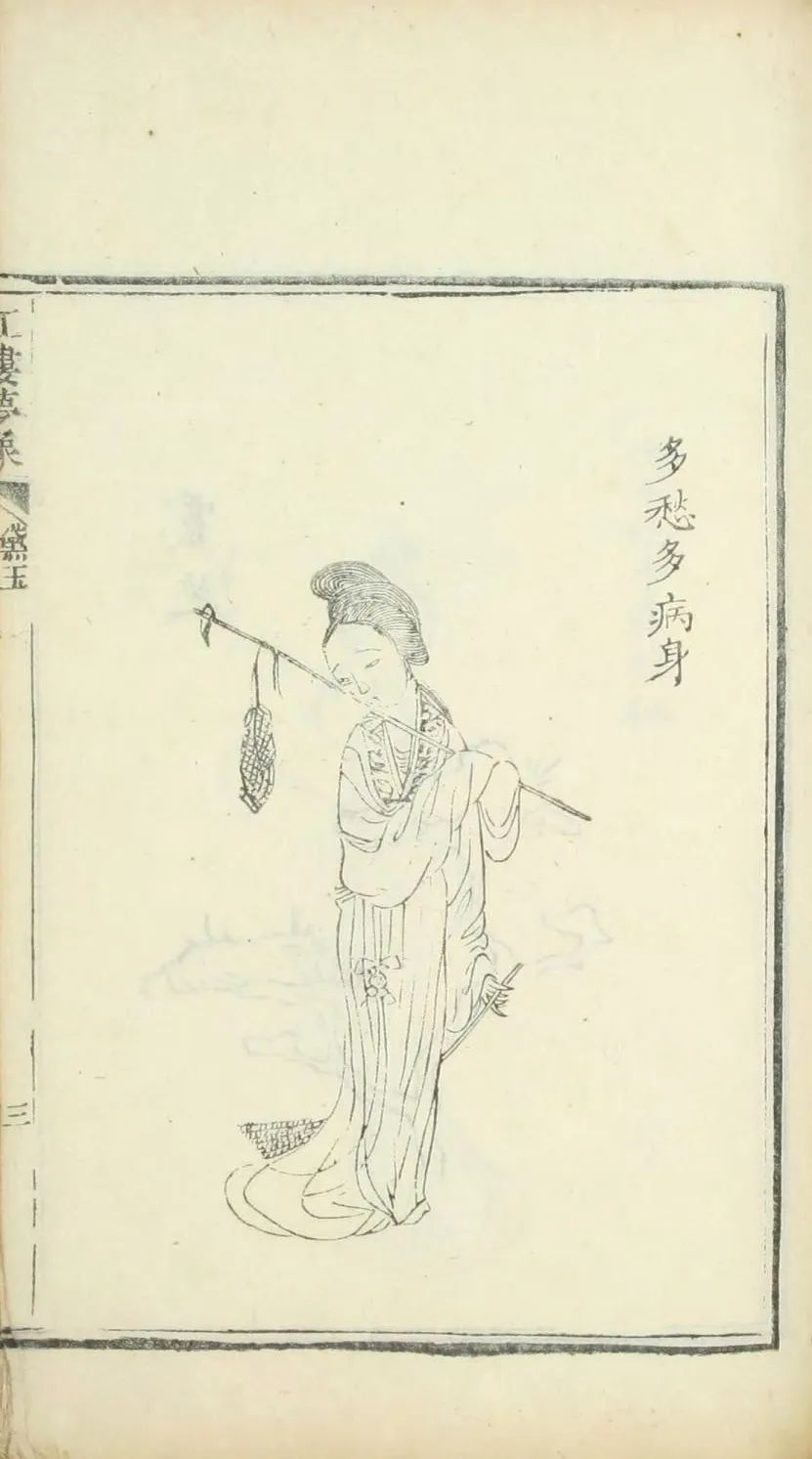
黛玉画像(《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插图)
再续影子说论,龄官是黛玉的“销魂影子”,无须多说;藕官是黛玉的“离魂影子”。藕官又是哪一出里的?杏花树下烧纸的那个,犯了大忌,多亏宝玉替她搪过去,原来祭的菂官,两人一生一旦,日久生情,竟假凤虚凰,用芳官话说,就是“疯傻”,说她“离魂”无疑最恰当。黛玉本是三生石畔绛珠草,雌雄合体,得换人形,修成女体,方才有一段世间情话。
下一问却有趣:“傻大姐是谁影子,曰是醉金刚影子。”这傻大姐无疑是荣宁二府的边缘人。甄士隐梦中所见,一僧一道带下尘世的“一干风流孽鬼”里并没有她,可见入不了籍的,却专给了一赞并一问。“赞”说:“傻大姐无知无识,纯然如彘,而实为红楼梦一大关键,大观园中落之故,实始于此。”果不其然,无知无觉中推形势转变,一是拾了绣春囊,引起查抄;二是透露绝密“掉包计”,可要了黛玉的命!涂瀛举三个典故,意为说明历史的偶然性:宋之逐狗,楚之献鼋,周之卖檿弧箕服者。第一例,出自《左传·襄公十七年》,宋国大臣华阅死后,弟弟华臣欺凌侄子皋比,杀总管,囚禁总管之妻,强索璧玉。宋平公大怒,以破坏宋国政令驱逐华臣,地方官则息事宁人,取退让之态,树欲静而风不止,忽有疯犬蹿来,民众合力追赶,破华臣家门而入,华臣以为前情爆发,惊惧逃亡。第二例,与前面所说“莺儿赞”里“郑灵之鼎”同典,借用目的则有不同,小缘由造成大祸端。第三例,《史记·周本纪》写,宣王时,有坊间女童歌谣:“檿弧箕服,实亡周国。”“檿弧”即山桑木制的弓,“箕服”为箕木制的箭袋,于是下令捕杀集市上售卖檿弧箕木的一对夫妇。夫妇俩闻风而逃,路上拾得女婴,即是褒姒,长成后入宫,为周幽王宠幸,“烽火戏诸侯”说的就是她。然后,“西夷犬戎进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戒幽王于骊山下”。总之,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傻大姐就好比宋之逐狗的“狗”,楚之献鼋的“鼋”,童谣中的“檿弧箕服”。读花人疑道,“人耶妖耶”,冥冥中似有使命交付,却昏昏然不觉,因此发问谁是影子,回答:醉金刚!醉金刚本名倪二,街头混子,以高利贷为生,通常惹不起,却有个义侠之名。贾府族人贾芸想在新园子里谋事,筹划伴手礼送主事的凤姐,到舅家的香料铺子赊冰片麝香,碰了钉子,万想不到,撞上倪二,喝了酒,定要借银子给他:“你我作了这些年的街坊,我在外头有名放账,你却从没有和我张过口。也不知你厌恶我是个泼皮,怕低了你的身份;也不知是你怕我难缠,利钱重?”所以,高低不要利息。贾芸有了银子,买香料敬上,果然得了个植树的美差,又因此邂逅知己小红,那小红且被提拔到凤姐跟前,可说风云际会。贾芸心里虽想着“改日加倍还他也倒罢了”,真到“还他”的时候,却爱莫能助。一百零四回,倪二趁醉耍赖,拦在贾雨村轿前,被带进衙门,家人求贾芸通人情。他以为只要姓贾都是通天的人物,岂不料侯门里也有三六九等,恰逢贾府多事之秋,那贾芸连门都进不去,又怎么说得上话。倪二自然以为贾芸不肯使力,发狠要闹他一场,有的没的抖落出来告官,“锦衣军查抄宁国府,聪马使弹劾平安州”由此发起,这就叫“醉金刚小鳅生大浪”,谁料想位高权重的贾家竟栽在这一节上。这倪二实不像《红楼梦》“情僧录”的人物,倒像《水浒传》里落了草的匪帮,且是个异类。依读花人的正反观,太虚幻境是实,红尘世界是影,按今天的话,就是逆行。傻大姐每一回肇祸,都在大观园,投到市井,就是倪二。
凡册子上人,都有前缘,仿佛天上的星宿化作凡胎,以文中人对文中人,犹不足以证明“影”和“形”。于是另起一大问,以史籍上的风流人物比拟。宝玉似武陵源百姓。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武陵人忽踏一地,仿佛蹈入世外,“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家家设酒宴请,留客几日,方依依送别。“怡然自乐”一句,格外像宝玉,园中人商议诗社,各人起个号,轮到他,宝钗先提“无事忙”,后又拟“富贵闲人”,最后落定“怡红公子”,都是他。家道渐呈衰微之态,先是秦可卿托梦王熙凤,提醒“否极泰来”的古训,然后闺阁中都动起来,献策开源节流。最不食人间烟火的黛玉,也向宝玉说道:“如今若不省俭,必制后手不接。”宝玉并不愁烦,只说:“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于是接着玩乐他的,这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喜聚不喜散的天性也像似武陵源人,来了个生客,一见如故,仿佛久别重逢。如此一个乐天派,历经离散无常,尤其生出虚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便由此而来。
林黛玉生来悲天悯人,深知有聚必有散,索性不聚罢了,也是前缘所定。三生石上欠下的甘露,要将一生的眼泪还他,必有个孤寂的身世、凄楚的遭际、感时伤怀的性子。与古今人作比,读花人对应的是贾长沙。贾长沙,贾谊,诗书过人,少年得志,汉文帝时入仕,步步高进。性情中人在官场,犹如林黛玉寄人篱下,可谓“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几经起落,后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不治,深为自责,本就是好哭之人,闲来无事迎风流泪,于是号泣年余,绝粒五日,终于泪尽身亡,人称“哭死”,年三十三岁。这是黛玉,宝钗呢,汉高祖!以帝王拟闺阁,看起来不妥帖,但不是有一句“治大国如烹小鲜”,反过来,则烹小鲜如治大国,就也说得着。初时,起兵响应陈胜、吴广草莽揭竿,再乘隙项羽亡秦,率军入关,攻占咸阳,先联手,后争天下,纵横捭阖,立皇位,开新朝,称汉,即灭大小诸侯——管窥之下,可否联想“莺儿赞”中设疑:“其后与秋纹麝月不知所终。”
不知读花人有意还是无心,宝黛二位都以西汉作比,在中国人心中,“汉”大约是欧洲人的古希腊,现代政治、经济、国体、艺术都可远溯到那时候,虽属人事,却在众生之上。贾宝玉则在世外。“贾宝玉赞”中,说宝玉之情既“为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又“为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尽之情”,是为无限对有限,批阅人梅阁的话,“是真菩萨,是大知识”。所以放到武陵源,归途上,渔人步步留下标记,却再无路径可寻,像不像太虚幻境?需有机悟才可得门而入。
湘云孰似?虬髯公,唐传奇中人物,风尘三侠之一。史湘云和林黛玉同是贾府的外家,但看平时,有说有笑,潇洒超脱,着了男装,就是个小子,那一位则“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明摆着不是同类。一个大剌剌的,另一个小性子,生出多少龃龉,算不上知己;与宝玉之间,前者兄弟之道,后者木石前盟,亦算不上怨偶。太虚幻境的册子,黛玉和宝钗并一副诗画,同一谶内,与湘云倒无关碍了。然而,中秋赏月,合家围坐,热闹人凤姐病了,李纨也告了乏,宝钗、宝琴回自家团圆,又听闻甄家抄了,兔死狐悲,秋风落叶,不禁意兴阑珊。式微之时,偏偏是这两个作伴,悄步退席,从“凸碧山庄”下到“凹晶溪馆”,说好些心里话。湘云说道:“就如咱们两个,虽父母不在,然却也忝在富贵之乡,只你我竟有许多不遂心的事。”黛玉应声:“无论事大事小,有理无理,其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况你我旅居客寄之人哉!”湘云生怕黛玉伤感,说不如联诗有趣,黛玉建议五言排律,因“咱两个都爱五言”,这却是新鲜,原来她俩早有款曲。夜深人静,水面黑影里仿佛藏了个人,黛玉说:“敢是个鬼罢?”湘云道:“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一石头过去,飞起一个白鹤,于是得句:“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就是这时候,忽来了个妙玉,暗地里听,觉得好是好,但一味“搜奇捡怪”,离题甚远,“到底还该归回到本来面目上去”。于是她提笔收结,即成就《右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三十五韵》。如此这般,风尘三侠均到齐,湘云虬髯公、黛玉红拂、妙玉李靖,三者皆有意会,更具神通。
探春孰似,太原公子!太原公子本是泛指皇族后裔有建树者,合乎这一美称者古来仅有两位,就成了专指人称。一是李世民,隋末太原李渊之子;二是唐末晋王李克用的公子李存勖,反败局而克胜。两位都生逢乱世,辅佐父辈基业。探春虽是女子,却有大志,五十六回中,凤姐有恙歇病,管家的职责落到李纨身上,王夫人深知大媳妇性子软弱,命探春协理,又请来宝钗。那两人只应付琐碎,意在安抚人心,唯有探春较真,趁此行使方针大计。探春没有秦可卿的仙机,但从眼前细枝末节着眼,窥见数桩宿弊,并从效率出发,制定可行性措施。然而,单凭她一己之力,扭转大趋势谈何容易,真正触底而起的一线生机,却是远嫁。太虚幻境中的册子将这一幕描绘得煞是凄楚,孤舟上的女子掩面而泣,诗云:“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注释以为“续书对探春结局的描写似与曹雪芹原意不合”。但画上还有两人放风筝,又仿佛怡然之情。曹雪芹前八十回里的第七十回,尤二姐风波始平,林黛玉重建桃花社,乘着诗兴,一并放起风筝。探春的一个“软翅子大凤凰”,正升到高处,从哪里也飞出一个凤凰,再一个门扇大的“喜”字带响鞭风筝,钟鸣一般逼近过来,与两个凤凰绞缠住,“三下齐收乱顿,谁知线都断了,那三个风筝飘飘摇摇都去了”。探春嫁的是镇海总制的公子,末尾,海疆靖寇班师凯旋,为善后事宜回京,探春随之,见她“出挑得比先前更好了,服采鲜明”,想必婚姻可人心意。且奏本称:“海宴河清,万民乐业。”皇上大赦天下,贾赦案复查,得以脱罪,家道呈现复兴的气象,应了当年风筝的兆头。因此,未必违了曹雪芹初衷。读花人所比太原公子应由此而起。
接下来是宝琴,比为藐姑仙子。“藐姑”是否当释作庄子“逍遥游”中的“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宝琴自小随经商的父亲走遍三山五岳,“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停”,不正合了藐姑山神人“游乎四海之外”。经姐妹们请求,以经过各省古迹为题,写绝句十篇,前八篇均有实地实物,末二篇“蒲东寺”“梅花观”,则出自虚构的戏文:一是《会真记》中张生与崔莺莺相会处,二是《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坟冢守庙,柳梦梅就是在此拾得杜丽娘自画像,随后人鬼相逢。宝钗以为这两篇无考,黛玉辩驳:“难道咱们连这两本戏也没有见过不成?”以此可见,宝钗为实证主义,黛玉是“信”的世界观。回头看“薛宝琴赞”,写她“可供,可嗅,可簪,而卒不可得而种,人间无此种也”。她入园时候与梅翰林之子已有媒聘,因此置身园中儿女哀怨之外,是为天人而设的现世缘。读花人有一解奇出异想,却合情合理,说宝琴雪中捧红梅一景,“雪”是“薛”,又非是“薛”,“梅”是“梅”,此“梅”又非彼“梅”,实是天然配偶。延及太虚幻境里的册子,不提宝琴,大约因她不是金陵人籍,若是有她,应就是这一帧了。涂瀛感慨园中姐妹们达不到这境界,诗曰:“玉京仙子本无瑕,总为尘缘一念差,姐妹是谁修得到,生时只许嫁梅花。”读来不禁戚然。
平儿古今人物孰似?春秋时郑国大夫子产,入《史记·循吏列传》,是为名相。郑国蕞尔小邦,与强大的楚国紧邻,好比虎口谋生,颇有点平儿处境的意思。用宝玉的话:“贾琏之俗,凤姐之威,她竟能周全体贴。”呼啦啦大厦将倾之际,从舅兄余毒手中救出巧姐儿,出离豪门,做田家之妇,人在末世,就不能视作落魄。按读花人说法,可谓“绚烂归于平淡”,诗咏“听罢笙歌樵唱好,看完花卉稻芒香”。回顾元妃省亲,隔帘向父亲说:“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秦可卿临死托梦于凤姐,交代永全之策,一是祖茔,二是家塾,有此两项,一旦有罪,祭祀产业是可不入官,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好有个退路。此时,不论是娘娘的期望,还是先知先觉,终在巧姐儿身上兑了现,平儿则是通渠引纤,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紫鹃的古今人似李令伯。李密,西晋人,晋武帝征为太子属官,因祖母老病,上“陈情表”婉辞,仁至义尽,情深意切,令人折服,而当祖母寿终完孝,即上任尽忠。读花人“赞”:“忠臣之事君也,不以羁旅引嫌;孝子之事亲也,不以螟蛉自外。”紫鹃之于黛玉,“在臣为羁旅,在子为螟蛉”。她最知道黛玉心思,谎称回南边,试探宝玉心意,随即提醒黛玉:“趁早儿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节,作定大事要紧。”因是“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黛玉何尝不懂,只是没人做主,自己怎么开口?薛姨妈和宝钗论婚嫁,都是越礼,遭到女儿一番驳斥。紫鹃自当其责,听薛姨妈玩笑把黛玉配宝玉,赶紧插嘴:“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结果碰一鼻子灰。黛玉去世,小姐伶仃一身,丫头岂能自寻出路?所以,“新交情重,不忍效袭人”;又原来是贾母身边的人,黛玉来后,拨给使唤,并不是自己的身子,因此,“故主恩深,不敢作鸳鸯之死”。生不得,死不得,不料想惜春出家,随之去了,称得上完节。又仿佛预演宝玉的归宿,取得科第,遗下胎息,遁入空门。
晴雯对应的是杨祖德。东汉人,本名杨修,出身世家,青年才俊,为曹操主簿,处理内外事务。众所周知,曹操是个善妒的人,几疑杨修僭越,痛下杀手,终年四十四岁。宝玉哭晴雯,说阶下海棠花无故死了半边,正是应在她身上。袭人原本劝了半天,此时却撑不住了,变色道:“便是这海棠,也该先来比我,也还轮不到他。”虽说读花人将凤姐对应曹操,可袭人的小肚鸡肠,与曹操也有得一比。
妙玉古今人孰似?答,阮始平,竹林七贤之阮咸,也就是阮籍的那个侄子,独孤乖戾,众人皆以为名士风流,超然物我。妙玉也孤僻自好,但多少掺些世俗气,比如刘姥姥喝的茶杯,宝玉建议送给刘姥姥胜过扔了它,妙玉道:“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我使过,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前面宝玉方才说过“世法平等”,出自《金刚经》,妙玉不会不知,行动却偏离了,可见她修行尚浅。后来的结局其实有伏笔,私以为高鹗接上了,但读花人不认,也是太爱惜的缘故。侯门千金,锦衣玉食,难免嫌贫爱富,林黛玉讥诮刘姥姥也挺刻薄,探春对生母赵姨娘循理不循亲。唯宝玉不同,人不分高低贵贱,只分水做的、泥做的,因此被划为武陵源居民,天下大同所在。以情而论,则是“至情”。
及此,心下不禁困惑,读花人为什么要用史上帝王将相来作比清俊女儿,分明是宝玉最嫌的须眉浊物,贾长沙、汉高祖、太原公子、子产、李令伯、杨德祖……人里的龙凤,才情出众,但还是为朝廷尽忠,宝玉极尽嘲讽的“文死谏武死战”,可不是玷污了这些女孩儿?是读花人另有衡器,脱不出现实社会的窠臼,所举人物全是青史留名,心中的真英雄,属读书人的局限性。然而,宝玉曾经遵父命,写下“姽婳将军”诗,称颂为王出征平靖天下的女子。按向来的原则,清清净净的女孩,沾了男子,便染上浊气,但此篇章出污泥不染,写出女子的英气,很有一番史湘云的风度,也像搜检大观园时候,探春和晴雯的杀伐果决。暗以为曹雪芹让宝玉写这命题作文,是为唱和之前黛玉的“五美吟”:西施、虞姬、昭君、绿珠、红拂,属正史的另一面。犹如湘云和丫头翠缕论阴阳,湘云说的“阴阳顺逆”,属辩证法,翠缕当然不解,却歪打正着:“开天辟地,都是阴阳了?”湘云再说:“‘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这就是个太极图。翠缕哪里懂得这个,只说:“这糊涂死我了!什么是个阴阳,没影没形的。”湘云举例道天地,水火,日月。翠缕方才悟过来:“怪道人都管着日头叫‘太阳’,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么‘太阴星’,就是这个理了。”因此,“古今人孰似”,实是读花人眼中的水中倒影。
古今人孰似,刘姥姥对冯权,对得很巧,都是野史中人物,掌故中的仙道。冯权出自《聊斋志异》“八大王”篇,本是贵胄,后来中落潦倒,无意间救了鳖精,得一双慧眼,识得世上宝物,发掘出来,转眼换了人间。刘姥姥的出身相仿,祖上做过京官,身后只留下一个儿子单传,家业萧条,回原籍乡下。刘姥姥实是外家,单凭旧时的一线瓜葛,求告上门。洞察世事,有胆有识,比得上一双“慧眼”。凤姐略施小慧,果真如刘姥姥的村话:“你老拔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虽未见大富大贵,但在乡里从此算得殷实人家。本事里有一细节,颇有些意味,就是冯权搜获的珍稀里,有一面镜子,佳人照过,便留影其中,姿色再上一等的照过,前影消去,更替近影。刘姥姥误闯怡红院,迎面就是一面镜子,镜子里的人,插了满头的花,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再是凤姐,比的是曹瞒,即一代枭雄曹操。“王熙凤赞”中,涂瀛称之“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又假设贾母健在,尚可以驾驭,犹如汉高祖辖制下的淮阴侯韩信和建成侯彭越,贾家还将有福寿。而王夫人和李纨,均是“昏柔愚懦”之辈,好比汉献帝刘协,被奸人欺凌,强人背叛,最终不得不禅让皇位给曹丕,终结两汉。因此,凤姐所作所为,勿论善恶,也是时势使然,评书人用了一个词,“骑虎难下”!贾府败落非一时铸成,溃崩则一泻千里,是运数已尽,真好似赤壁之战,也应了秦可卿梦中谶语: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可见出读花人对凤姐的心情相当复杂,爱不能,恨不能。而此后的袭人,单看古今人孰似吕雉,就知道尽是嫌恶,别无其余。
与天下英雄比拟一番,再换一盘棋,安到坊间,红楼中人如何安置。答曰:宝钗是妻,晴雯是妾,芳官等是子女,紫鹃为臣,湘云为友,平儿“宾”之,探春则“宗师”,宝琴“君”,宝玉“佛”,黛玉“仙”,刘姥姥“俳优”,莺儿等“奴”,凤姐“贼”,袭人——“蛇蝎”!这一番排序,不止离了太虚幻境的风月籍贯,还脱去荣宁两宅的远近亲疏,只从人格品性出发。说是“读花”,实是“阅世”,也是“梦”的两界。一界“无”,即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僧一道所携一干风流冤家,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落尘于另一界——“有”——将宿命演绎成悲欢离合。
涂瀛身在“有”中,深谙世态常情,难免怀恻隐之心,于是自问:“王夫人逐晴雯芳官等乃家法应尔,子何痛诋之深也。”要说“痛诋”,言辞极为尖利,“王夫人赞”中专以王安石和贾似道作比,前者乱天下,后者失天下,前者“有才而自恃其才则杀人必多”,后者“无才而妄用其才则杀人愈多”,并且不惜恶咒:“安得有后哉。”特别说明贾兰是李纨的福气,非王夫人所属。针对“家法”则答曰:“红楼梦只可言情,不可言法。”若按法论,宝玉不在书斋,却在花园,仆从丫头,交游姐妹,混迹脂粉群中,如何说得过去?既有这一误,袭人就不当是同类,晴雯也不当有罪。如此“颠颠倒倒”,显露出作书人的“危心”,道统与人欲的两难。还是现实主义作祟,不能像《牡丹亭》的柳梦梅和杜丽娘,从生向死,死而复生,一元世界里互通有无。“红楼梦”里,《牡丹亭》却是不可入闺帷的。
再有一大“危心”,即黛玉的家资。贾家财政紧张,宫里的太监时不时来打秋风,凤姐都要央鸳鸯暗里取出老祖宗的私房典当,实已经相当难堪了。急切之下,贾琏说出这么一句话:“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虽不能当作明证,但约莫有两条线索,一是当年黛玉奔丧,由贾琏护送,经手善后事宜;二是财产的规模,衡量出黛玉身价之巨。涂瀛由此判断,黛玉去世,理论上遗产应归于贾家,实际却由凤姐领受。所以,“黛玉之死,死于其才,亦死于其财也”。倘若循此踪迹向下走,问题又来了,贾府的财富体量,单是贾母的陪嫁,都可挽狂澜过难关,三二百万不过小巫见大巫!真要是个富二代,黛玉和宝钗扯平,或不至于落选,看起来黛玉并无这份筹码。于是又生一问:“或问林黛玉聪敏绝世,何以如许家资而乃一无所知也?”答得很好:“若好歹将数百万家资横据胸中,便全身烟火气矣。”也因此“以为名贵”,又因此“为宝玉之知心”。所以,这笔钱还是不提为好,有了它,连“红楼梦”都变质了。必要时候,不得不排除逻辑的干扰,走出一条旁路。
就因著书人的“危心”,种下了“病”,所谓“病”,今天的话说,就是“硬伤”。普遍认识,多在人物的年龄,常常对不上榫卯,比如元春和宝玉,惜春长不大,巧姐儿倏忽成人,李嬷嬷是个老妪,怎能做宝玉奶娘?然而,读花人却以为红楼阁主有意为之,“故作罅漏示人,以子虚乌有也”。就又回到太虚幻境。再看跋者邱登文末记时,“道光己酉大雪前三日”,令人想起贾宝玉向贾政作别的那一幕,可不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二〇二五年五月七日,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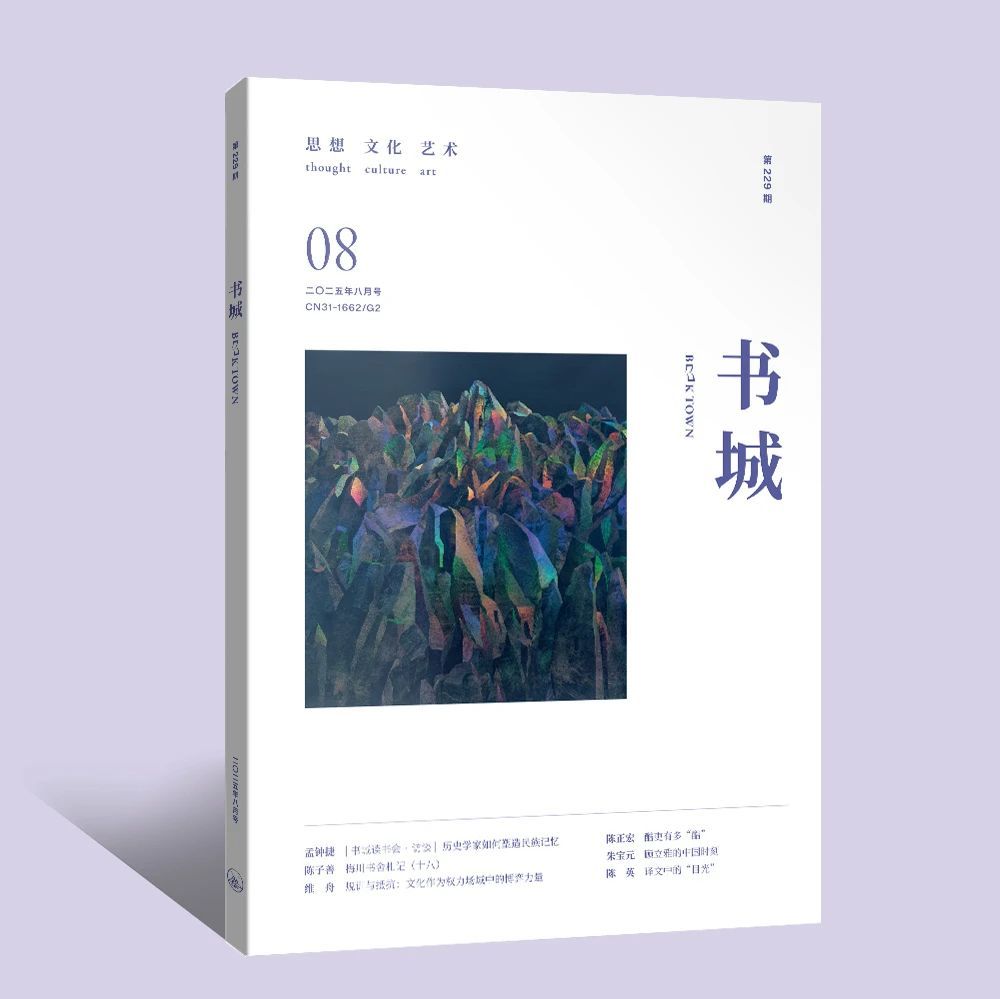
本文转载自《书城》2025年8月号。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