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还要从1949年说起,意大利于该年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创始成员,这不仅是在军事上成为了美国的盟友,也等于肯定了美式的经济发展形式。紧接着,这座亚平宁半岛上的文艺复兴摇篮,在1952年和1957年相继成为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创始成员,遵循着马歇尔计划的脚步,开始了本国的战后经济复苏。然而快速进步的浮华之下,却埋着社会矛盾的引线,出生于1949年的弗兰科·贝拉尔迪可能也无法想象,最终于1968年爆发的工人/学生运动,会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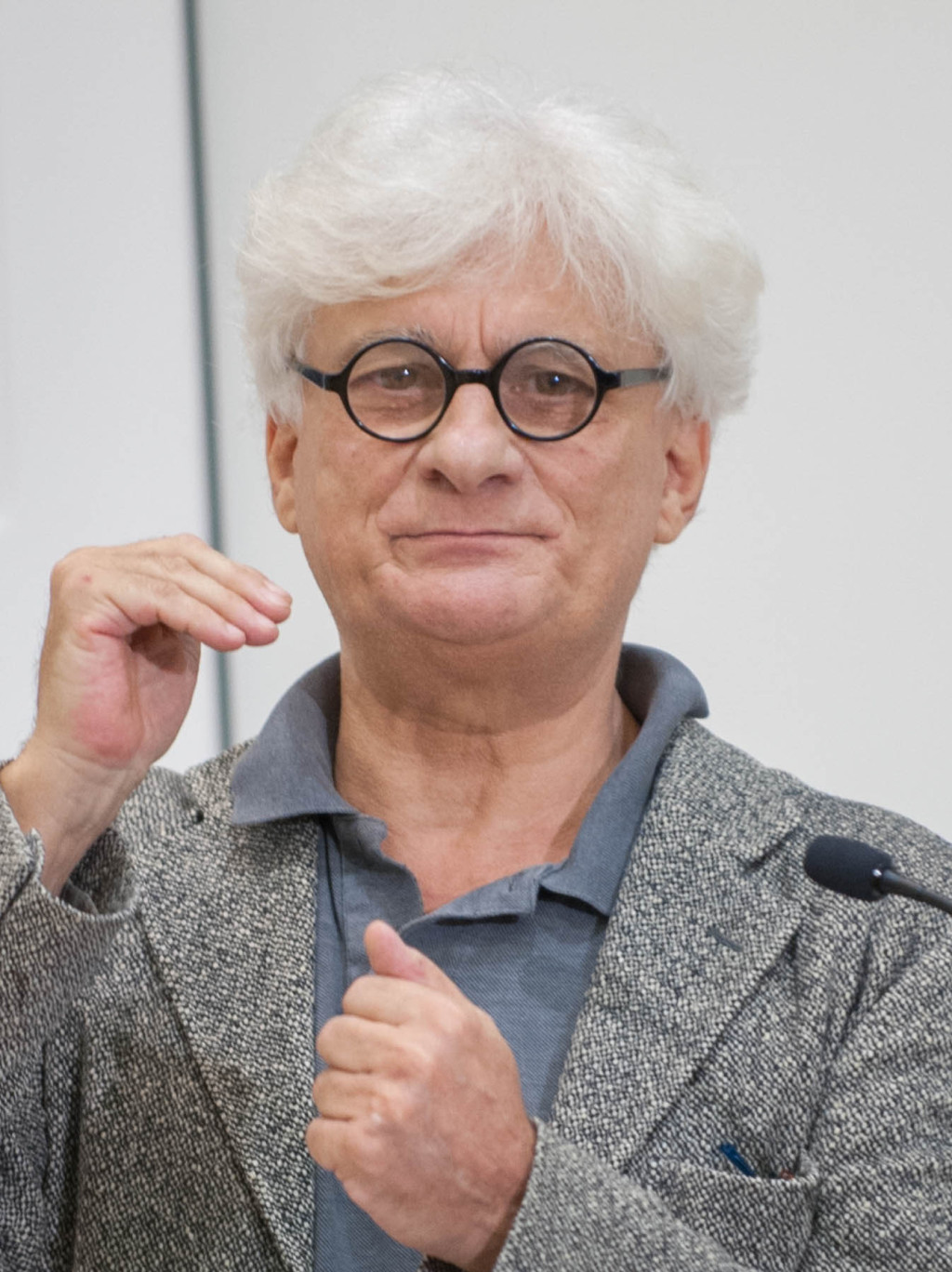
弗兰科·贝拉尔迪
相较于弗兰科·贝拉尔迪,“比弗”(Bifo)这个自学生时代起就使用的签名更为大众所熟知。或许他在刚加入意大利工人主义组织,并投身1970年代“火热之秋”运动时,还没有意识到作为一名年轻的社会运动者会有何种的危险。1970年他的第一本著作《反对工作》(Contro il lavoro)不过就是延续了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真正威胁到他自身安全的,则是他于1975年和1976年分别创立的地下刊物《穿/越》(A/traverso)以及意大利首个海盗电台阿丽切(Radio Alice)。从此,传媒技术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成为了他思想与行动的核心。1977年该电台被迫关闭,而比弗也因“通过广播煽动叛乱”在博洛尼亚被警方通缉,于是他被迫逃亡巴黎,并在此结识了菲利克斯·加塔利与米歇尔·福柯。虽然之后返回过祖国,但比弗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便移居美国纽约,为当地还有米兰的杂志撰稿。
作为社会活动参与者,比弗走访了世界各地,从印度到墨西哥、尼泊尔,甚至中国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与各类媒体的不同接触中,他的左翼理论更加深入地触及了精神分析、赛博朋克以及当代艺术与未来等多种主题。而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25年7月出版的《灵魂在工作:从异化到自主》,则是比弗自身理论研究的经典代表作。他在表明资本主义是如何利用新型手段,对人类的身体与精神进行持续剥削的同时,也没有遗忘自己作为工人主义思想家该有的人文关怀。可理解了灵魂为何以及如何在工作的根本原因,就真的能找到通往自由的解放之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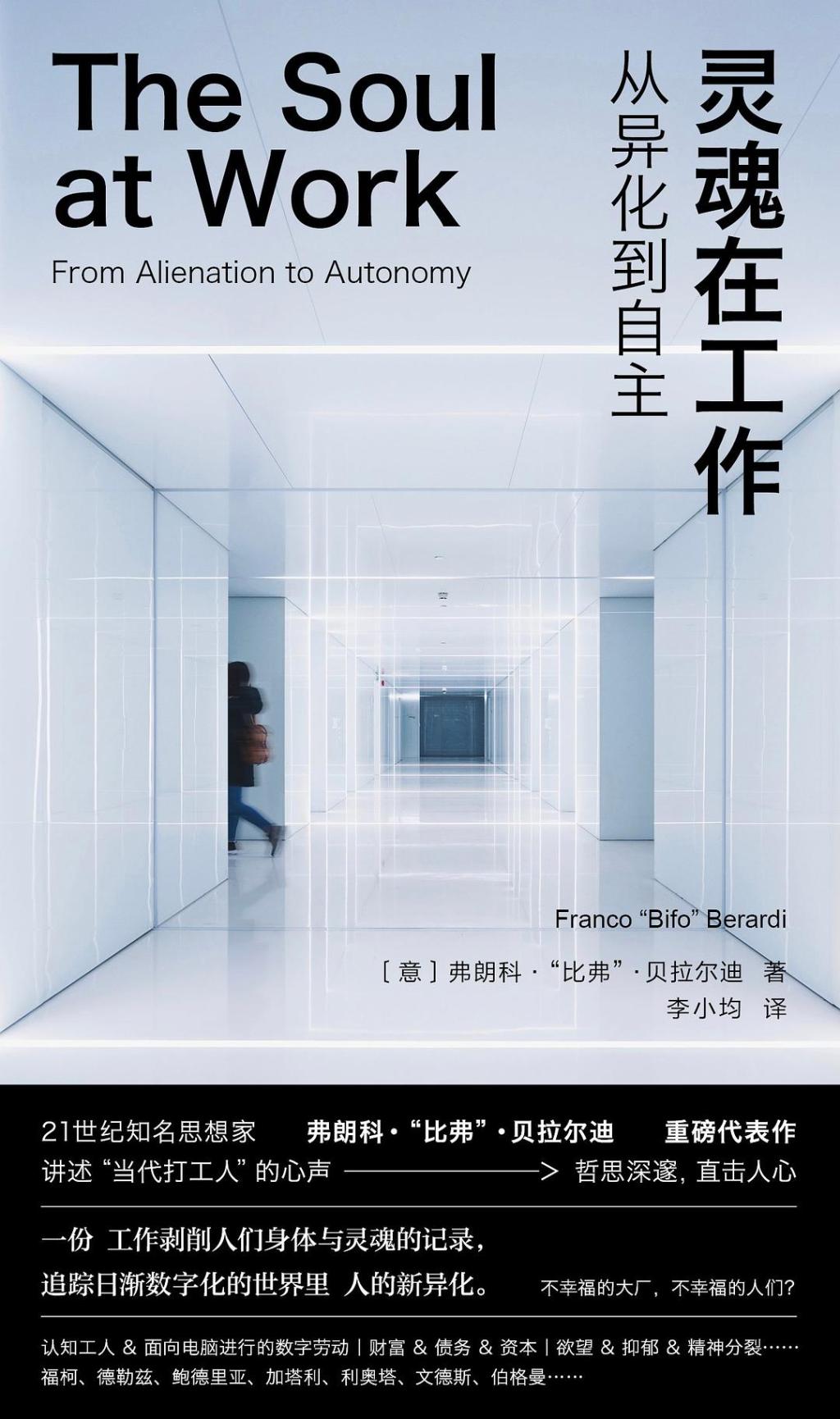
《灵魂在工作:从异化到自主》书封
一些比弗引用的概念
首先是“灵魂”,虽然比弗一直遵循着马克思主义,但他仍然像所有思想家一样,会回到古希腊时期去寻找最原初的概念,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唯物主义让他确定了灵魂的意义——“灵魂是有生命的气息,把生物性的物质转化为生命性的身体。”(本书前言第1页)于是灵魂与身体组成了有羁绊的共生关系,在21克的科学神话被打破之后,灵魂是身体的一个思想器官这种论断,或许可以让人文主义者更好地思考个体与世界的联系。
其次便是“知本阶级”,马克思早在1858年的《机器论片段》中就预言了一般智力会成为最主要的生产力,而随着技术的进步,数字和网络让传统知识分子的面貌焕然一新,跃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体。这个群体所进行的知识劳动,也不再按照传统的一二三排列顺序,与一般的社会劳动区分开来,而是在空隙之地进行着一种重要的焊接工作,确保生产过程和社会交流的通畅。知本阶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认知劳动的社会性肉身,时刻保持着专注,无休止地贡献着智慧。
接下来就是“异化”,虽然唯物主义从根本上是反对唯心主义的,但并不妨碍比弗以此种观念来架构“异化”的概念,他模拟了一场青年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论战,还将萨特和马尔库塞也拉了进来,最后将对人类本真性的预设融入进了历史存在中,“异化”已经不仅仅是本质的丧失、被否定、被剥夺、被暂停,更是人类之间的分离与失落,是人对物的屈服。
还有“工作”,如今工作所涉及的方式、环境与条件,和半个世纪前工人阶级斗争时所反抗的工作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面对屏幕,手敲键盘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趋势。数字技术更是开辟了一种劳动的全新视角,手工劳动逐渐被执行编程指令的机器取代,脑力劳动则正在创造真正的价值。虽然劳动仍然是依赖工作内容和工资收入,以出售个人时间为内容的社会活动,但仰仗高科技的各行业从业者,早已不是传统工业生产线上的工人——虽然工作内容可以简化,但却无法互换。生产线工人在八小时之后,可以从“临时死亡”的状态中苏醒,但高度特异化且深度个性化的工作,却为如今的工作者们竖起了坚固的壁垒,而其中永远没有定时八小时的闹钟。
一条比弗串起的草蛇灰线
可以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意大利工人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好的继承者,他们紧抓住“劳动”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工人/学生的二元组在进行着抗争,之所以团结学生这个群体,或许是因为在工业工人阶级看来,他们不仅会成为未来的自己,也是行使理性来确保人权、平等和普世法律的知识分子们的雏形。然而这对组合的任何成员都没有料到,进入新世纪后,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对策,工业工人逐渐淡出舞台,知识分子不再是自由个体,而是成为了大众社会的主体,融入进了一般生产过程。
科技成了资本的新爪牙,用各种新颖的形式取代了单个劳动,传统工人被降格成为次级生产者,失去主体地位之后,工人形象好像变为了一具无生命的残骸。而资本借助“企业”实现了一种共和,对立逐渐消失,企业反倒成为了可以将劳动发展成事业的投资者。事业成功的过程也伴随着财富的积累,然而在消费社会的趋势下,“财富”从身心愉悦的质量,逐渐偏向了资本的经济学口舌所给出的答案:财富意味着拥有让我们能够消费的手段,即金钱、信贷和权力的可能性。(本书第93页)这样一个片面的答案,却几乎主宰了全世界——人们总想着积累购买力,却没有意识到花费了更多的时间,而留下来供自己享受的时间却越来越少。
在多年与媒体接触的过程中,比弗发现社会的神经系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逐渐匮乏,取而代之的是商品化的、符号化的补偿。在这种补偿中,“幸福”也改变了味道,这两个字逐渐有了某种集体性意义,通过广告进行碎片化的布道,让人们将自己的欲望投进经济理论和政治行动的系统中,并且坚信,只有成为消费者,才能最终抓住左躲右闪的“幸福”。
新自由主义倡导的竞争看似是件好事——每个人都有资格为自身争得利益,市场为竞争者们完全开放,国家不得过多干预经济活动。然而这蒙蔽不了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双眼,比弗认定新自由主义颂扬的市场不过就是个童话,经济从来无法和权力完全分开,表面繁荣的背后不仅有暴力和谎言,还带来了间断性的金融危机。竞争、市场、自由、危机……这一系列资本主义的新手段,像一剂毒针,扎入人类的身体,直达呼喊着本真性的灵魂。
即便电影有了声音,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依旧是对工人生活最透彻的艺术表达,上世纪二十年代无声的机械性动作一直延续至六七十年代。可如今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之下,话语却过载了,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在线,因为这关乎我们的工作,工作连接着购买力,而超强的购买力就可以带来幸福——我们就是这样深深陷入了线路和屏幕的泥泞之中,逐渐放弃了对隐私的保护,这是一种侵占,更是围攻。对物化的屈服在数字光缆的持续鞭笞下,变成了对非现实化的俯首称臣。
同样的,灵魂对时代性异化的改变也有了不同的反应。当工人们还在重复每天超出八小时的可替代劳动时,灵魂带领身体反抗的是生产流程,中断的是自身的劳作,机床停了,锅炉的气焰渐逝,火车不再喷出汽笛声,这时候的工人群体是团结一致的。而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咒语太过动听,就连灵魂也投入了工作,它再没有力气抵抗诱惑,只能气若游丝地让身体有些非一般的动作,异化不再是对人类本真性的警告,而是被悲惨地归为精神病理学,冠上了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新名字。在新的时代,工人阶级不复存在,认知劳动者虽然是智慧的无产阶级,却如一盘散沙,对于曾经高喊共产主义的比弗来说,或许哀莫大于此了。
一些比弗看到的希望
作为思想家的比弗先搬来了救兵——欧陆哲学自1970年代起在重新构建概念的坐标,福柯、德勒兹、阿甘本等,都帮助这位出身博洛尼亚的革命者重新思考已经变形的权力结构与社会主体。而在一系列后现代的话语之中,鲍德里亚那具有颠覆性的观点与概念(“仿真”、“内爆”和“灾难”等)不仅充满了理论与政治的内涵,还如同利剑一般,直指当下的现状。
在鲍德里亚的指导下,比弗确认了真实场景的被抛弃,摄像机、胶片与屏幕让真实的场景与人进入到仿真的环境之中,蒙太奇成为了支配者,现实则成为了荒漠,屏幕上投射出的,是无休止的符号。在鲍德里亚看来,进入拟真和拟像之后,欲望和力比多被机械化了,但对于这种欲望权力的理论,比弗并没有苟同,他在德勒兹和加塔利那里找到了更好的解释:欲望是历史的核心领域,因为在这一领域内,那些对集体心智的形成、因此也是对社会进步的主轴而言至关重要的力量,他们通过并置或冲突在此相遇。(本书第150页)比弗很好地提取了《反俄狄浦斯》中的方法,哲学景观中的“无器官身体”让他看到了主体性成形的过程,佐以社会批判概念的精神分析,也让他认同了阿兰·埃伦贝格在《疲于做自己》中所讨论的、无法否认的事实:依赖竞争的抑郁症,其实是一种社会病理综合征。
比弗是个非常优秀的理论研究者,他没有对哲学家们的著作断章取义,而是巧妙地提炼出了可以为己所用的核心部分。当下时代病理的特征是虚拟的欲望对象在无限激增,直播间、购物平台无时无刻不在用创意十足的广告宣传着琳琅满目的消费品,身心愉悦的享受一直被拖延,力比多能量逐渐干涸。如果屏幕不再闪亮,恐慌就会袭来,对狭小空间的过分关注削弱了人们对自身和他人的理解,或许过去人们还试着理解对方,但如今连这微弱的意图也将消失殆尽。
比弗希望现代人能看到新自由主义为社会带来了怎样的效果,他引用了福柯的“生命政治”、安东尼奥尼、伯格曼和文德斯的电影作品,他想为大众深挖这背后的运行法则,想让大众意识到,限制竞争的法律规范和社会规则看似被消除了,但其实是被简化了,我们的生活——包括医疗、教育、性、情感、文化等——都变成了遵循供需法则的经济空间,如今我们不仅身体被套上了锁链,就连灵魂也已屈从于技术生产。但如果我们的脚步稍稍慢一些,先放下对消费的追求和对经济的狂热,重新思考“财富”的真正定义,或许就能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被削弱过,它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改换面貌,让我们不断地跳入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漩涡中,使自己忘记了何为享受自然,何为相互合作。只有从“竞争”这个幻象中挣脱出来,资本主义的根基才会有所动摇,而人类本真性的自由才有可能浮出水面。
结语
比弗绝不是乐观的,虽然他在本书最后说资本主义持续五百年的系统最终会崩溃,然而这五百年间,人类的经济观已经逐渐固化,资本主义面对各种危机只会越发地得心应手。在比弗看来,全球经济崩溃是一个机会,人们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间,为了工作而放弃了太多,既然社会结构已经变得松散,不如就趁现在,解开生产过剩的双重束缚。他幻想着让收入脱离经济学框架,改为人类学框架,而灵魂的自由,可以依托“美学范式”,让哲学与艺术渗入混沌之中。这样就可以使人们更加关注自身,释放出知识、智慧和情感作为财富的一部分,而非强迫性的无用劳动。不得不说,思想家的展望,确实是既美好,又可爱。
当曾经的工厂变成了如今的大厂,手中的螺丝刀换成了键盘和鼠标,就算有好心人告诉那个准备签署学费贷款合同的年轻人,魔鬼只是换了副面孔,他就藏在银行的身后,等着你签下 “资助学业”的灵魂契约,可这个年轻人还能有更好的选择吗?就算我们都知道996背后的不道德,但对于一个没有依靠、就业困难的学生来说,即便是有漏洞的劳动合同,仍然是一份难得的工作机会。打工人面对所谓经济和政治的困境,可能觉得还是“干更多的活,赚更多的钱,但别去思考社会”这种话更动听些。当人们的认知水平有所提高,并不会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工人阶级一般,团结一致,为了提高工资和工作环境水平而奋起反抗,只会是将自己投向下一个工作场域,继续一种深谙此道的“恶性循环”。自由经济的毒已经太深,深到这种秩序根本无法被打破。进入21世纪,比弗仍在高喊“反对工作”,而他向往的共产主义,也覆盖上了共和的糖衣,所以他只能将任务转向构建自主。只不过他也清楚,他从未放弃的马克思那“个人的自我实现”和他畅想的“快乐的独特化”,已经成为了社会的精神分析治疗过程,而这过程,无尽且漫长。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