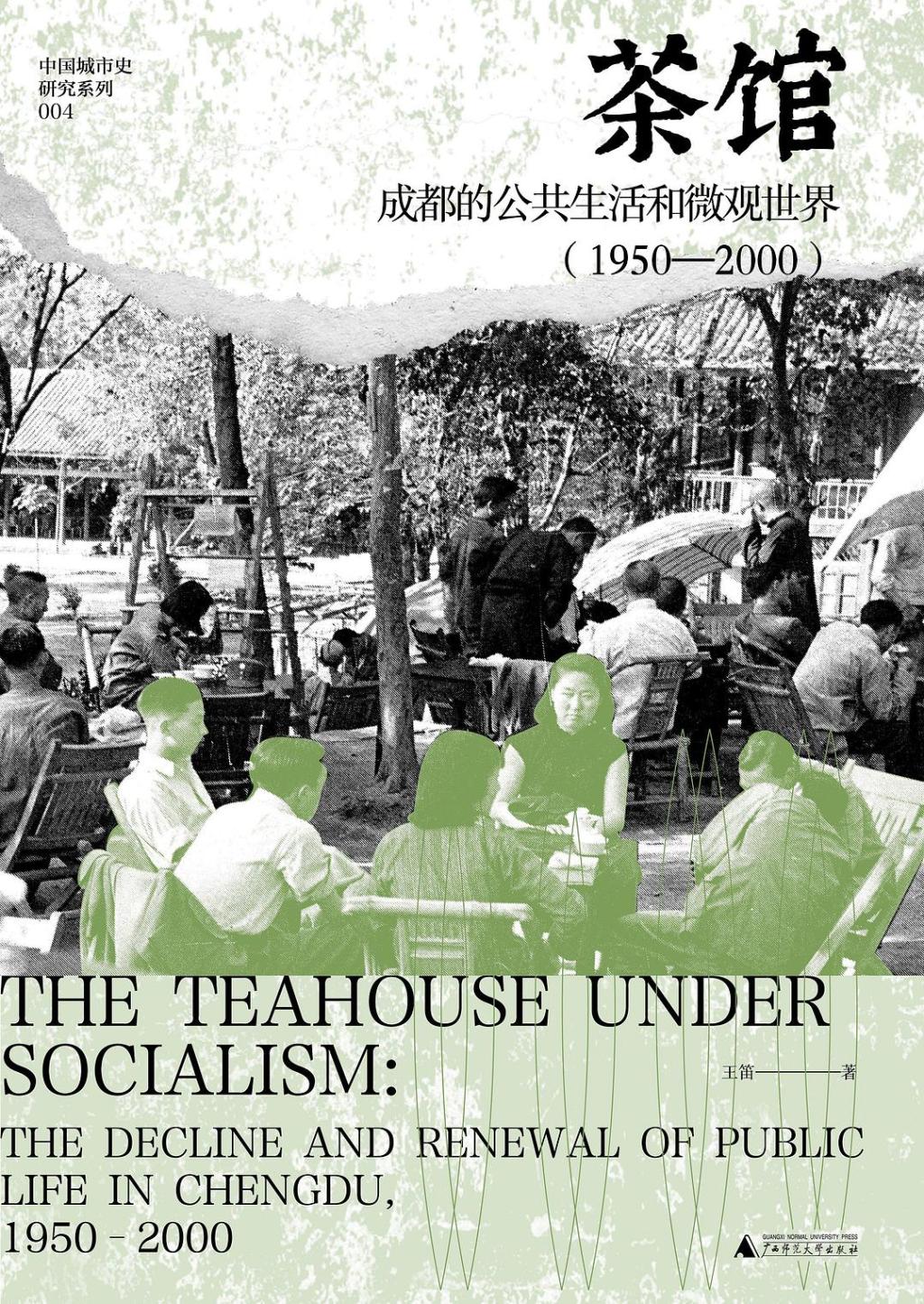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王笛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2025年8月出版,444页,89.00元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是川人王笛的研究成果,其目的在于保存成都茶馆的功业,为了不至于因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茶馆里发生的那些令人感叹的过往的痕迹不致失去光采,特别是为了把它们盛衰的原因给记载下来。
了解希罗多德《历史》的读者,看到这段文字一定会会心一笑。是的,我借用了古希腊写史的开篇套句。我以为,这段文字用在王笛身上再合适不过了。王笛写成都街头文化、世相百态,现在继《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中文版付梓后,屡经曲折续篇《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简体字本终于问世了。两部茶馆,横跨百年,仿佛一面镜子折射了成都乃至中国的历史。续篇虽然与前篇旨意一贯,但于文献资料之外,还融入了作者实地调查的成果。在希罗多德那里,历史这一概念与后世的理解径庭有别,是调查研究及其结果的意思,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因此将《历史》视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先驱。比较而言,本书不但是历史学著作,还具有社会学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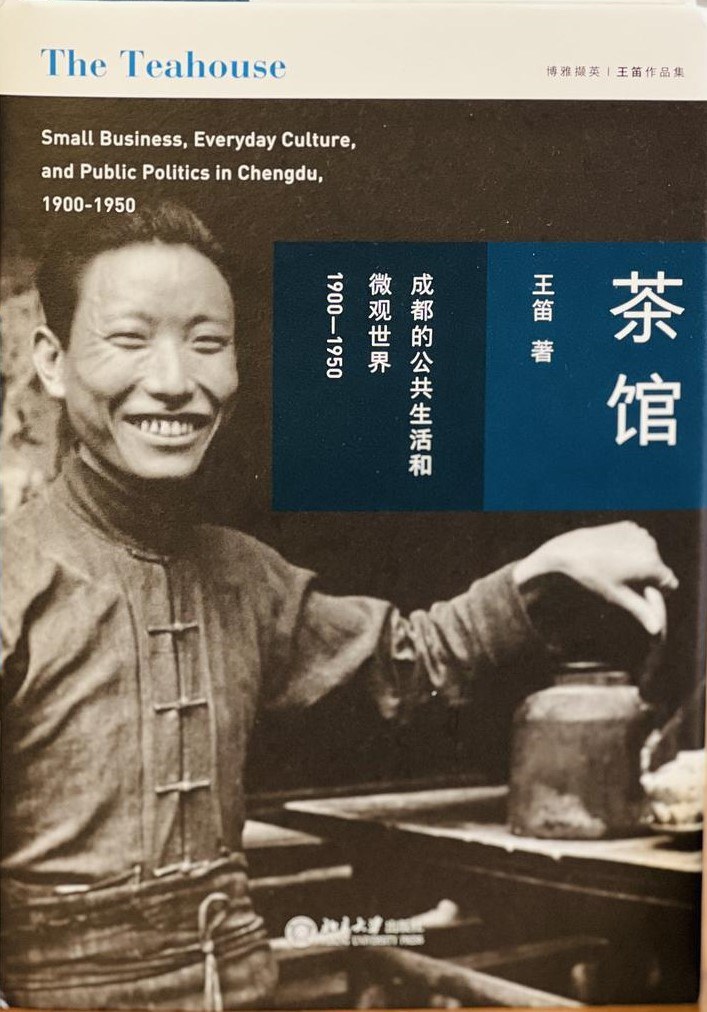
王笛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虽然早在赴美留学前,王笛即已成名,但他的写作风格很美国化,是用社会科学手法研究历史,我将其归为“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范畴。在第一章导论里,作者开宗明义地交待了写作动机——揭示二十世纪后半叶成都茶馆所经历的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76)及改革开放时代(1977年至今)的二次变化。茶馆作为人群聚散的场所,如何研究呢?王笛在回顾了国外相关理论后提炼出两个贯穿全书的关键概念——公共生活和政治文化。
关于公共生活,历来有不同的理解,作者采用的是桑内特(Richard Sennett)的定义——私人家庭之外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的内与外都有政治,作者倾向于林·亨特(Lynn Hunt)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使用的较为限定的定义,即将政治文化限定在“革命”范畴内。王笛的考量显然是基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来的,这样保持了解释和实际间的紧张感。我历来认为欧美社会科学理论是从相对透明的社会中抽取的,在用以解释重叠交错的中国现象时需格外小心。不消说王笛深知此中要诀,在理论检讨完后立刻转入研究对象上,行文中偶尔回应既往研究,是为研究王道。
本书第二至四章涉及共和国成立初期茶馆的命运。这是一个不断革命的年代,一个追求匀质化的时代,最终包括茶馆在内的一盘散沙被整合在新的政治装置中,一举克服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体》所慨叹的困扰现代国家的“有限性”(limited)难题。于是,在一个趋于政治学家邹谠所说的“全能主义”(totalism)的时代里,作为实在场域的茶馆迎来了整合的命运——同业公会被改造,茶馆被整顿,党团分子、哥老会成员等不符合社会主义理想的人被清除,伴随茶馆的“阶级转向”,茶馆里上演的戏剧亦被规范化,最终作为无用之物而黯然消失。

《茶馆》插图
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历史老师很认真地说当代人最好不要研究当代史,因为离得太近,不能保证“客观性”。离得远了,就能保证“客观性”了吗?否。现在大家知道,历史研究客观与否与当下的远近并无直接关系,而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那句名言——一切真的历史是当代史——也不是时间远近之意思,是指意识投射在人的当下行动之中。但是,老师的提醒总是有一定缘由的,疫情期间去世的“年鉴学派”第三代费罗(Mare Ferro)认为历史书写存在三种沉默:第一种沉默与正统性相关,在涉及正统性起源问题上,书写显得“不透明”;第二种沉默是加害者内在化的、心照不宣的与社会共有的沉默;第三种是受害者对难言之痛的沉默表现为集体失忆。就当代人写当代史而言,由于涉及方方面面的利害,会有一些不得已的沉默,因此,善读书者会顺着作者视线继续阅读空白。

《茶馆》插图
本书第五至七章讲改革开放后的茶馆复兴。在去匀质化的微波下,茶馆回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伴随消费水平的提高,新式茶楼兴起,茶馆的功能趋于多样化——不仅有茶师,还有挖耳匠、卖报人、擦鞋女,等等。作为区域公共生活空间,消费者除了本地人外,外来群体——“打工人”构成了一个惹眼的存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如何使大众消闲符合公共的道德准则成为一个问题,王笛研究了茶馆中的方城大战——麻将,将其置于当事人之间、居委会、区域社会乃至国家层面进行考察,揭示了本书主旨所在的公共生活和政治文化之间的龃龉。麻将,最终博弈的不是“智巧”而是“运气”,反映了人性对不确定性的渴望,大概不会打麻将的缘故,王笛对此忽略不论,如果我写,当会浓墨重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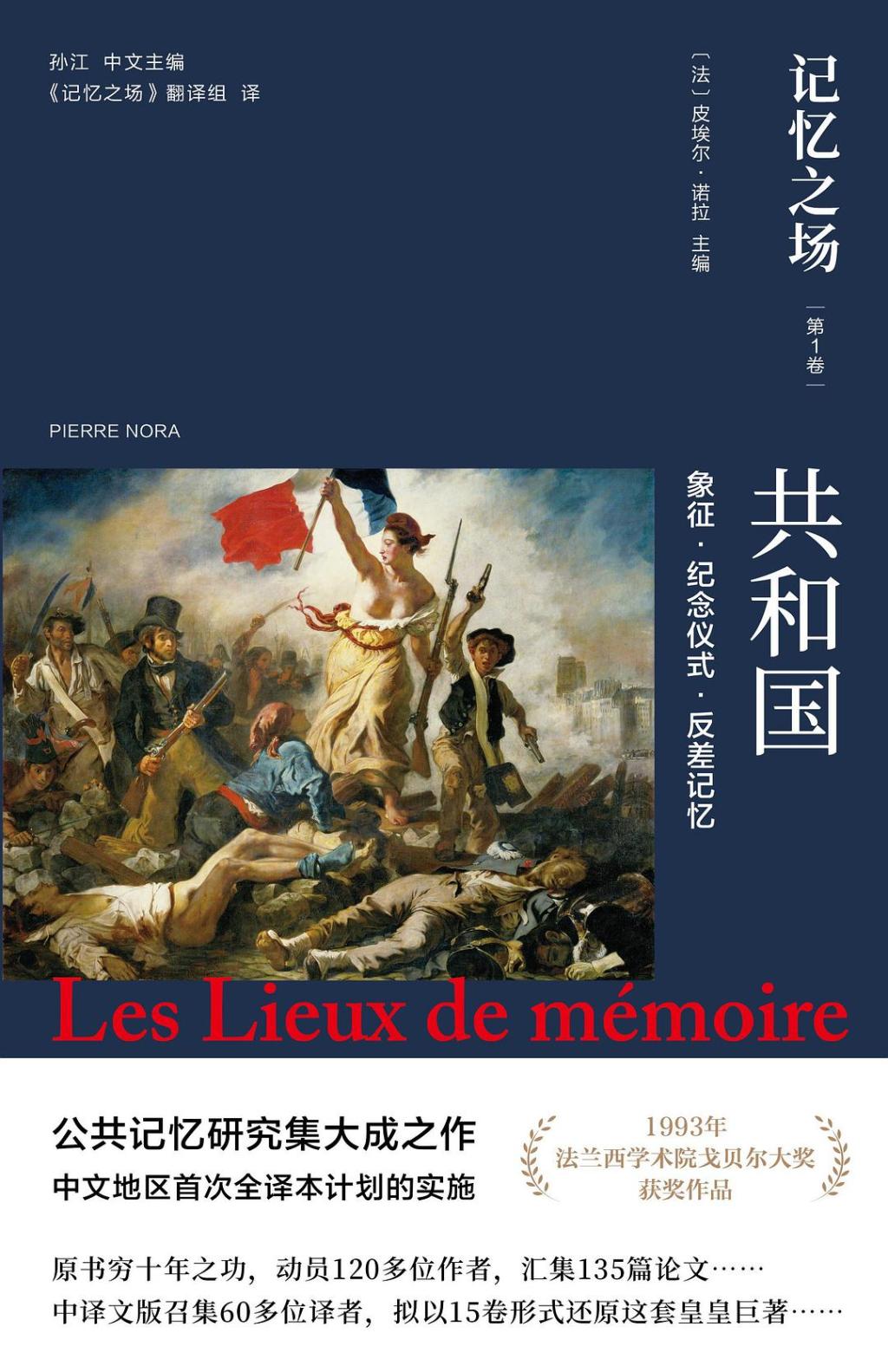
皮埃尔·诺拉编《记忆之场》
通过以上考察,王笛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呢?第八章回到第一章的问题提起,回答了茶馆在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所具有的三重属性——既有社会性又有政治性还隐含公共领域的特征。茶馆投射的是一个变中不变的中国,或曰不变中有变的中国。在“历史加速消失”(皮埃尔·诺拉语)的当下,本书研究的五十年不要说对零零后一代很是遥远,对于同时代的笔者也正变得越发陌生。6月,我在牛津大学与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聊天,我问她正在研究什么,她答曰即将开始关于新中国初期历史的研究。对沈艾娣教授的最近印象还停留在《危险的翻译》的我闻言沉默良久。研究当代史,讲述当代史,就是抢救加速消失的历史。王笛的著作逻辑清晰,叙事简明,预留前沿,我往年讲社会史课必会推荐给学生阅读。如今,在我的推荐书单上又多了一本书。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