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马识途回忆道,新政府成立后,茶馆被认为是隐藏着污秽与懒惰的地方……实际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我们可以取茶馆之益而去其之弊,当然,这样的话茶馆的弊处将会完全被消除,茶馆将成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以及宣传教育的场所……
但茶馆的数量确实是大大减少了。成都作为一个大城市……茶馆的消失比农村集镇更为迅速。根据雷影娜(Regina Abrami)的研究,非成都居民不能获得营业执照,店主和小贩也被要求每年续签营业证,而“工商局的干部们有着极大的权限,去定义什么是合法私有生意的规模与范围”。
官办的地方报纸不再像民国时期那么关注茶馆,有关的报道很少,但有时也从其他角度透露一些茶馆的信息。如1956年《成都日报》发表《不怕困难的茶社工人》,介绍锦春茶社烧瓮子工人龙森荣,报道他这年3月被评“行业二等劳动模范”后,在劳动竞赛中“又作出了新的贡献”。他用锯末代替煤炭烧茶炉子,经多次试验,终于成功。锦春茶社一天可节约煤120斤,全年达4.3万多斤。随后他又向其他茶社推广这个办法,帮助13家茶社改进炉灶。回忆资料也从另外的角度揭示了茶馆的状况。如沃若回忆小时候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一家茶馆烧开水,家里的所有财产除身上的衣服外,就只有一床被子、一张油布、一个铜罐。每晚当最后一位顾客离开后,父亲便把四张桌子拼在一起,铺上油布作床,脱下衣服作枕头,每早天不亮就被几个喝早茶的老爷子吆喝起来。

据一位老市民对西御街德盛茶馆的回忆,该茶馆有两间铺面大小,店堂宽敞明亮,分成前后两部分:前堂多为零星客人,后堂主要为老顾客。该茶馆是20世纪50年代初开办的,生意颇为兴隆。德盛茶馆每晚都有相声演出,当时成都颇有名气的相声演员都在那里登台,但由于内容重复,听众渐少,后换成竹琴演出。有一位姓杨的竹琴艺人,约四十岁,胖而面善,有弥勒佛之相。他可唱全本《慈云走国》,声情并茂,“紧张处让你提心吊胆,伤悲处让你潸然泪下”。《慈云走国》讲的是宋朝慈云太子被奸臣加害,流落民间,后在忠义之士的帮助下,历尽艰难,扫除奸佞,重振朝纲的故事,很受听众欢迎。中间休息时,由妻子挨个收钱,他则闭目养神,或抽烟喝茶。
又据阿年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他父亲经常在晚上带他到街口的茶铺里去听评书,他在那里结识了几个来茶铺捡烟头的小伙伴,不久他自己也加入了捡烟头的行列。碰上演出精彩的评书,听众多,烟头也多,有时一次捡的烟头足够父亲抽两三天。后来阿年住西沟头巷,地处市中心,在文化宫对面,他家隔壁便是中心茶社。那时一般人家烧柴灶,他外公觉得锅里烧的水有烟味,不能沏茶,所以一天至少要去茶馆买几次开水。没有钱买茶叶时,便去茶馆倒“加班茶”(顾客喝剩下来的茶)。阿年十分乐意去茶馆买水,这样可以借机在那里玩一阵,不必担心回去挨骂。有时耽误久了,就找若干理由,像水没有烧开,或茶客多开水不出堂之类。其实他外公知道他只要一进茶铺,便要看热闹。那里有算命的、打竹琴的、耍魔术的、看“洋片”(“西洋景”,小孩从一个孔看里面的各种图片)的、卖麻辣兔肉的,形形色色,“只要一扎进去,半天也出不来,大概这中心茶社便是我童年包罗万象的游乐宫了,甚至就连今天的夜总会、卡拉OK厅也绝没有如此精彩”。
作家黄裳喜欢在成都坐茶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茶馆也都光顾过,如人民公园里临河的茶座、春熙路的茶楼、在旧花园基础上改造的三桂茶园等都去过。他说,20世纪50年代成都的茶馆有很多优点,“只要在这样的茶馆里一坐,就会自然而然地习惯了成都的风格和生活基调的”。那个时候的茶馆,都还有民间艺人唱各种小调,打着木板,讲着故事。还有卖烟的妇女,她们拿着四五尺长的竹烟管卖烟,竹烟管也可以出租给茶客,由于烟管太长,自己无法点火,所以还得替租用者点火。也有不少卖瓜子花生者,他们穿行于茶座之间。修鞋匠也在那里谋生活,出租连环画的摊子生意也不错。尽管经过了改朝换代,但茶馆传统的生活方式仍在继续。

另一位成都老居民张先德指出20世纪50年代的茶馆还是同过去一样,大量坐落在街边、河边、桥头,还有相当部分在公园内,少数在市中心者布置较高雅。但最能代表成都茶馆者,还是那些大众化的街角茶铺,所以当时成都人爱说:“到口子上去啖三花!”张先德不无夸张地说,如果要评选成都人最经常使用、最能代表成都人的一句话,恐怕这句话当之无愧。掺茶师傅仍然继承了先辈的敬业精神,他们多为青壮年男子,技术高,服务好,头脑活,反应快,加之又善社交,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机行事。不过那些小茶铺的店主往往兼做堂倌。
又据张先德回忆,他过去住的小街上,百步以内就有两家中等规模的茶馆,即万花楼茶社和百花茶社。前者有三间铺面和一层楼面,茶馆还可以利用街沿和街对面空地增设茶座,因此可同时接待上百客人,但该茶馆在20世纪60年代初关闭,改作酱园铺。百花茶社比较简陋,亦可容纳数十人,经常拥挤不堪,特别是打围鼓、讲评书时,一二百人济济一堂。那时经常有人来坐场打围鼓、说书,或拉二胡、弹扬琴,“茶铺借此吸引茶客,艺人则借此谋生”。正如本书第三章所讨论的,政府虽然试图取消这项活动,但仍然不能完全成功。讲评书一般在晚上,有时下午也有,讲的多是《说岳》《水浒》《三国》《聊斋》《济公传》等节目。尽管政府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传统节目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下来。随着政治运动的日益激进,到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前夕,说书人也不得不紧跟形势,讲述《林则徐禁烟》《敌后武工队》等革命节目。百花茶社一直维持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即使是在最困难的年代里,茶馆生活也依然存在。黄先生出生于1956年,在东大街度过了孩提和青少年时代。他家的隔壁便是一家茶馆,他经常透过墙上的一个洞来窥探茶馆内的活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茶馆里仍有木偶戏、“打道琴”和长长的水烟管。夏天,一些小伙伴会到茶馆里拉一个巨大的吊扇来赚钱,扇子悬在梁上,下面的人用绳子拉动扇子为顾客送风。吴女士也回忆说,在20世纪50年代,她的一位同事每天早上5点去茶馆,这位同事当父亲之后,把小孩也带去茶馆,甚至在冬天也不间断。喝完早茶后,他才回家吃早餐,然后再去单位上班。后来他搬了家,离常去的茶馆有好几里路远,但是他还是坚持坐公共汽车去那里喝早茶。以上这些故事都显示了茶馆生活对人们的吸引力及重要性。
民间艺人和茶馆有着密切的依附关系,艺人得到茶馆同意,约定了演唱时间、演出收入分配办法等,便可以开演了。一般茶馆中茶资和评书费“各自收取”,艺人和茶馆之间“尚未发现其他关系”。其他演员人数较多的表演形式如演戏等,艺人还需向茶馆交付房租、电费及其他费用等。演唱时间一般都在下午和晚上。据一份1955年的报告指出,在所有的民间艺人中,评书为最多,占54%;其次是金钱板、荷叶、竹琴、扬琴等,占33%。演木偶、灯影戏者少得多。对茶馆里面演出的内容,调查报告认为这些演出多是“未经整理过”“含有毒素的旧唱词”,因为他们演唱的目的是“招徕顾主,维持生活,因此不顾形式内容,乱说乱唱,甚至表现下流庸俗动作”。不过调查报告对曲艺也有正面评价,表示有部分艺人的说唱是“经过整理推荐的优秀传统节目”和“反映现代生活的新书词”。
“书棚”是另一种类型的娱乐场所,那里整天都有说书和其他曲艺表演。书棚一般设施都非常简陋,多在城郊,观众和艺人多是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的农民。调查报告称书棚里“乱说乱唱和下流表演比较普遍”,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最为不好”。这份1955年的报告还说他们演唱水平一般不高,流动性大,“生活作风不好”,甚至指责有少数艺人“与流氓盗窃分子有联系”。报告中列举若干人名,其中一个是金钱板艺人、四个是清音艺人,“由于卖淫、偷窃、诈骗等均被拘捕劳改过和正在劳改中”。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乡场上的演出相比城内,历来较少受精英和政府的直接干预;但在社会主义时期,它们无疑都在新政府的严格管理之下了。

去茶馆喝茶的是各色人等,小贩和耍小把戏者也可在茶社招徕顾客,还有“一等功力深厚的旧式老茶客”。说他们“功力深厚”,并不是指他们的品茶水平,而是指他们“以茶铺为家,整天屁股难离茶座,像有钉子钉着,或放了一块磨盘”。他们到茶馆,并非为茶,甚至也不是玩棋牌、听戏曲或弄鸟雀,而是“属意茶铺那种习惯了的气氛”。他们一大早来到茶馆,一碗茶,一张报纸,便可打发几个小时,困了则用报纸捂着脸打瞌睡。这种坐功,可以同和尚的“坐禅”或“打禅”相媲美。张先德回忆这些茶客时评论道,他从小到大,在茶铺里“见识过各等人物,其中不乏有意思的人、能人、高人”;但他印象最深者,是那些“坐功极佳的老禅客”。人们或许认为他们“是无用之辈,穷极无聊”,但也说不定是“闹市中的野鹤闲云”。在他们那里,似乎隐藏着无尽的奥秘,他们能够“处变不惊,于无味之处品尝人生的味道”,可以说把“成都人的闲适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甚至可以成为区分外地人与成都人的“重要标志”。
在20世纪上半叶,妇女是否可以进入茶馆便一直是人们讨论的问题,她们也逐渐争取到茶馆的使用权。然而即使到了20世纪50年代,女人坐茶馆仍远不如男人普遍,特别是人们对女学生和女青年泡茶馆仍然颇有微词,认为她们不高雅、太低俗。人们对中老年女人坐茶馆倒是习以为常,这些女人“多是家庭妇女中家务事较少,或不大经佑家务的老耍家”。
茶馆里人们的穿着和外表也昭示着时代的变化。着长衫者日益减少,中山服、列宁装等逐渐流行,那个时候时兴在上衣口袋内插钢笔,人们可以从中猜测其身份,所以当时有个说法是:一支钢笔小学生,两支钢笔中学生,三支钢笔大学生。
不仅是一般民众,甚至大学教授们也是茶馆的常客,如四川大学历史系蒙文通(1894-1968)教授的课,“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掏钱招待吃茶”。他的考试也别具一格,并非他出题考学生,而是由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问题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果问题问得好,蒙先生则“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若有学生登门问学,“他多半邀对方去家隔壁的茶馆,一边吃茶,一边讲学,一边操着带些盐亭土腔的四川话得意地说:“你在茶馆里头听到我讲的,在课堂上不一定听得到喔。”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蒙文通此举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
政权的更迭可以在短时期内完成,但生活方式的改变需要很长时间。光顾茶馆是一个在中国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了许多年的习惯,在共产党执政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尽管茶馆业在逐步萎缩,但人们的茶馆生活仍然在继续。茶馆仍然是各阶层人士喜欢光顾的地方。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人们仍然光顾茶馆,虽然此时人们已经感觉到政治的疾风暴雨到来前的压抑。公共生活被国家密切关注,特别是被那些国家权力中较低层次的代表,如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等机构关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给了茶馆致命一击,当茶馆和其他公共生活的因素消失之后,成都的茶馆和茶馆生活也跌至20世纪的最低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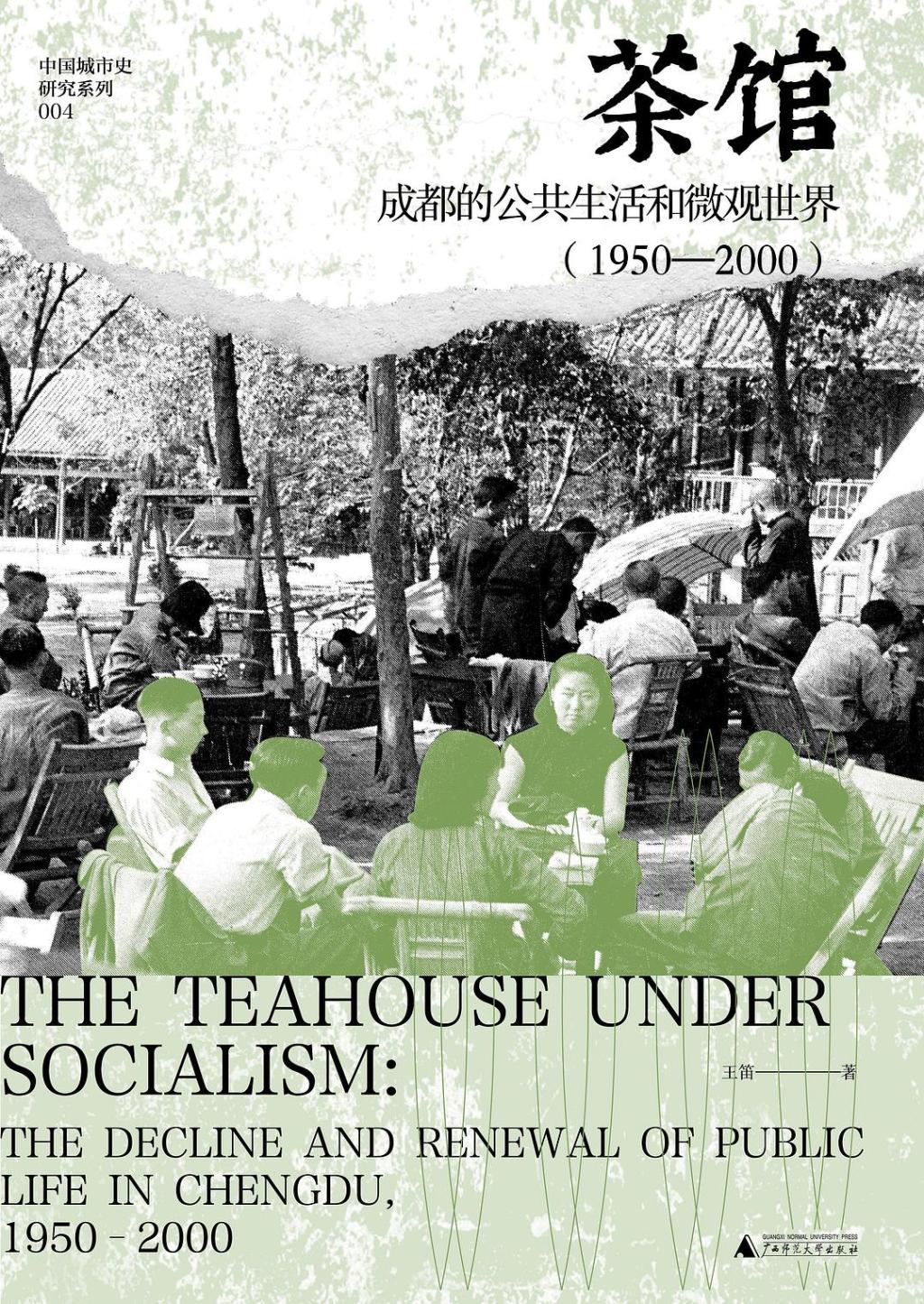
(本文摘自王笛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