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大突破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会涌现大批通过科技创新获得爆发式成长的企业,切切实实将前沿科技转化为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能。
2025年7月18日,宇树科技开启上市辅导的消息,引发一波“宇树概念股”行情。也再次带火了创始人王兴兴2019年带“狗”融资,却遭投资人“一言而拒”的聊天截图。彼时,恐怕王兴兴自己也难以预料,只在并不太久的5年之后,他的公司就跃升为年收10亿的现象级创新龙头。无独有偶,最近在国内访问掀起热潮的黄仁勋,当年也未必敢想,他顶着几乎整个华尔街的压力孤注一掷的CUDA,将使英伟达刷新全球的市值纪录。
对此,很多人会归咎于资本的短视。然而,在高知扎堆、目光锐利的学术界,这种“例外”也并不鲜见。此次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演讲引发全网热议的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的神经网络研究,曾长期被当时的主流AI界排斥。卡塔琳·考里科(Katalin Kariko)的mRNA研究,甚至无法保住她的大学教职。当然,所幸他们的结果是大圆满的。他们那些曾经坐“冷板凳”,甚至连“冷板凳”都挤不上的研究,不仅结出了耀眼的硕果,更是在近十年取得了非凡的商业成功。2024年和2023年的诺贝尔奖,也足以慰藉他们曾经饱受冷遇的坚守岁月。
在人类科技史上,这样的黑马逆袭还有很多,只是在近年愈加频繁,成就也愈加瞩目。这种反复上演的“偶然”,也引发了深刻的反思:为什么最后跑出来的,往往并不是起步就资源满载、顶配顶流的“大而强”?其中有相当比例,最初只是在舞台边角的“小而美”,甚至是坐在台下“冷板凳”上的“小而丑”。
由此可见,在新一轮的科技浪潮中,科技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的成功范式正在加速演变。这值得我们关注和探究,并据此重新审视政府在科技创新和产业生态构建中的角色作用。
“小而美”,美在何处?
不可否认,资源富集的“大而强”有着更加稳健的成功概率。这种“大投入等于大产出”的逻辑,自工业大生产时代起,就有着强大的现实基础。回顾我国的科技创新历程,依托众所周知的集中精锐力量的“大兵团”攻关模式,我们迅速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然而,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大而强”渐渐显出不再能够“包打天下”的现实局限。
暂且不论管理学中的“大公司诅咒”,单从科技创新规律看,重大突破常常诞生于被忽视的交叉领域,因此在科学史上的颠覆者,往往都是昔日的“边缘人”。这也印证了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的核心。然而,这显然也与“大而强”常居舞台中央,集“万千宠爱”的情况大相径庭。
那么,“小而美”究竟“美”在何处,何以能成为“大而强”的结构性补充?究其根源,其优势源于“小而美”名称蕴含的两大特质。
首先,“小”在于切口小。诚然,规模不“大”是“小而美”显而易见的特征。但从更本质来说,“小而美”的小是指“专精”的特质。因为领域窄小,所以在专业上更易专注,在行动上更加灵活,在组织上更易管理,在产业上更易协同,在竞争上烈度也相对更低,从而更有利于练成自己的“独门绝技”。相较之下,“大”的一方常因更长的战线和更高的组织融合难度等问题,反倒颇有些“大有大的难处”。
其次,“美”在于闭环能力。既然能称得上是闭环,那就意味着市场有需求、服务能供给、运营可自足。这不仅验证了市场对产品服务的真实接受度,也考验了公司的基本运营和发展能力。而这些也恰恰正是一些资本快速催熟的“大而强”最为欠缺的素质,也明显迥异于高校的实验室模式。
值得说明的是,对于这样的“小而美”来说,“专精特新”可能是一个更贴切的标签,而有别于通常所说的“隐形冠军”。因为“小而美”,既无需刻意“隐形”,也未必需要追求“冠军”。正如初创期的宇树科技,既没有大牌专家领衔,也谈不上多么独树一帜。类似地,由全华班打造的DeepSeek也是,虽然没有光环,但经过市场淬炼,在专业细分中是真的能“打”。更重要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更使得精悍的小团队具备了在数字世界中实施不对称、跨维度竞争的能力,让“小而美”具有实现更大抱负的可能。
构建“小而美”友好的创新生态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政府大力扶持创新龙头,在具体科技路线选择上集中突破的策略亦非罕见。客观而言,不论是“大而强”还是“小而美”均得以从中受益。但显然前者的受益程度通常更为显著。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资源过度集中可能造成创新生态的单一化和脆弱性,导致那些非共识、非主流,却独具潜力的创新方向难以获得充分支持。更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过度介入可能会干扰市场对技术路线的自然筛选过程,引发“虚假繁荣”或导致技术路径的锁定风险。
在世界科技创新史上,因过度押注单一技术路线而错失其他重大机遇的案例比比皆是,从前苏联倾力脱离市场要素研发的三进制计算机与电子管小型化研发,到日本政府联合主要企业举国推动的第五代计算机,其教训都足以为鉴。
当前,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招商工作,对招揽“大而强”往往不惜重金。这固然有推动地方发展的合理动机。然而僧多粥少之下,卖方市场带来非理性竞价和内卷式溢价,无疑会显著推高了地方财政风险。因此,相较于在不确定的赛道上豪赌单一项目,将更多确定性资源投向构建“小而美”友好的创新生态,无疑是更可持续的战略选择。毕竟,稍加回想就不难发现,那些最终长成的生态型巨头,其源头大多正是本地孕育的“小而美”。
构建这一生态,有赖于三个方面施力。
首先,建立适应“小而美”价值的评价体系。“小而美”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小”中彰显其“美”。因其扎根于窄小的利基市场,远离热点领域,技术路线不一定符合当前主流的学术审美,甚至场景都不一定为大领域同行专家所熟知。那么,如何引入更加广泛、平衡、包容的评价机制、更为敏捷的科技布局战略,以准确识别和支持这类创新便显得尤为关键。现实中,追逐热点、包装概念,远比扎实创新要更为容易,更为“高效”。而能让那些坚持不蹭热点,敢于独辟蹊径的“小而美”获得公正的评价和支持,显然是检验创新生态成色的关键标尺。近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及部分地区推出的面向“非共识创新”支持计划,正是对此问题的积极回应和有益探索。
其次,探索激发“小而美”涌现的机制平台。科技创新的生命力在于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速这一转化是各国科技战略的核心关切。科技创新的生命力在于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速这一转化是各国科技战略的核心关切。这方面,国际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路径借鉴: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Fraunhofer-Gesellschaft)构建了强大的技术转移平台体系;英国SEIS计划通过税收撬动早期风险投资;美国《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和日本JST的“A-STEP”种子加速器则极大激发了高校专利转化的活力。国内实践亦在深化:一批新型大学积极探索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新模式;地方政府层面,各类概念验证中心、科创平台加速布局,技术经理人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共同为“小而美”的萌芽与早期成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三,完善针对“小而美”扶持的平衡之道。现实来说,“小而美”的首要难题是“活下去”。先求存,后能美。可喜的是,科技金融体系这两年正在加快健全。尤其是国资背景的“国家队”“地方队”积极践行“耐心资本”理念,“投早投小”早已深入人心。
然而,市场化机制始终是企业优胜劣汰最高效、公正的裁判。技术上说,基金难点在于应对高风险和长周期的。但从技术经济逻辑上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大力扶持技术创新的同时,最小化对市场信号的干扰?如何在倡导宽容失败的同时,有效防范潜在的道德风险?如何在长周期中的“耐心”等待中动态评估、敏捷调整?这些问题目前各地都还在探索,期待尽快能有思路和模式上的突破。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支持之外国家正大力构建的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以及大力倡导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展模式。相比直接的金融滴管,这些极具特色的制度创新,兴许是更贴近市场逻辑的支撑模式。
这些年里有一种用词的惯性,似乎无“生态”,不“文章”。但知行之间,总会比较大程度地考验智慧和定力。但其实这也并不难琢磨明白。就像在科技创新生态中,参天大树“顶天立地”固然引人瞩目,可叹可贺。但之所以能称得上是“生态”,离不开芳草如茵、新苗破土、百花竞放。让“小而美”得以良性成长以至“铺天盖地”,何尝不是一种科技发展“新范式”,何尝不能汇成“大引擎”,何尝没有“大未来”?
(作者钱学胜为复旦大学智慧城市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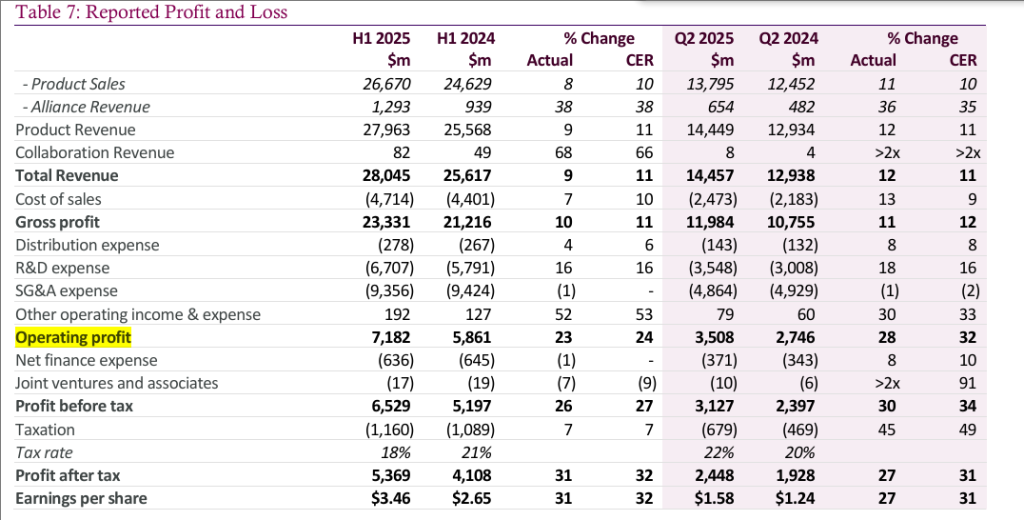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